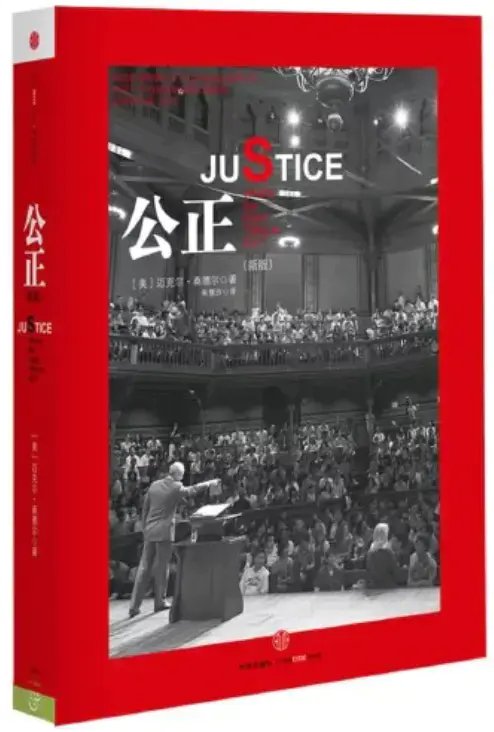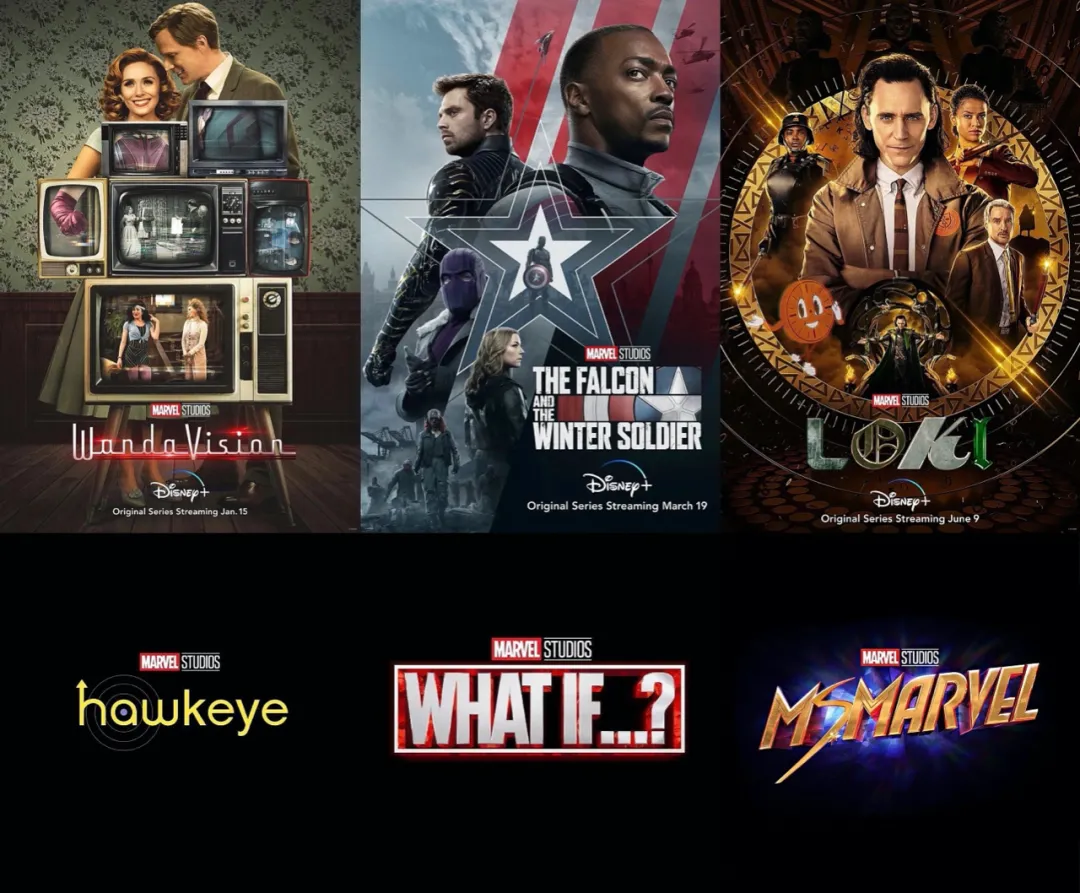影评比电影好看吗
《戏剧电影报》,《看电影》,《电影世界》,《环球银幕》。 ——这是中国纸媒黄金时代里,最好的几种电影媒体。而《戏剧电影报》则是其中最先冒起又最早倒下的那一个,久违的豆瓣红人“九只苍蝇撞墙”发来了下文。在今天,他忆起了这份报纸的当年事。
前网络时代的电影媒体私人记忆
文/九只苍蝇撞墙
作者简介:影评人,电影学者。
一到年节,我的豆瓣首页就变得聒噪起来。
这是国产电影一年里的最关键时刻。很可能在此之前一两个月,宣传机器就被实力雄厚的财力启动,通过各种媒介尤其是所谓的新媒体(巨大流量的小视频APP和微信衍生出的自媒体)对普通老百姓实施处心积虑又没头没脑的狂轰滥炸,感觉当年第三帝国戈博士见识了也会心惊胆颤自叹弗如。
不少以写关于电影的文字为生的名字,平日里对欧美电影大师的作品都赞赏有加分析得头头是道,但一到大年初一,忽然都变成了小品二人转电影的狂热粉丝。需要等这七天假期过去,那股“在骨头里挑鸡蛋”的激情才会逐渐平复回归正常。
我不太记得起这种电影评论与片方合作赢两次的大好局面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也不太敢分析这中国大陆市场独有的运作机制给电影、电影媒体和电影评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但我记得当初走进这个行当的时候,写电影评论和做电影媒体这个事儿还是另外一个样。
01
香港刚刚回归祖国那阵儿,我从学校毕业在家闲着,有一天在报亭买了份北京文联办的《戏剧电影报》,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看到一则招聘编辑的启示。上学的时候我在学校录像厅里渡过了不少时光,感谢那位不拘一格放艺术片的老板,我看过了从《重庆森林》到《情书》,从《野战排》到《教父一二三》的各种影史重要作品,此时便不知天高地厚觉得有责任通过新闻界向广大人民群众推广一下自己熟悉并喜爱的那些片子。
《重庆森林》中,“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这句著名台词本身,也似乎已然过期
报社编辑部在百万庄《解放军报》招待所里租了几个房间当办公室,去面试才知道这是顶着《戏》报的刊号,引入个人投资专门介绍外国电影的一份周刊,起名叫《戏剧电影报——环球综艺》。
彼时市面上开始流行起了盗版VCD,业余时间出现了大批蹲在街边小贩的摊位边和胡同口音像店里挑碟的群众;应运而生的,看了这些碟的青少年们开始对影片里的外国明星产生了自发的崇拜情绪。新闻界的有识之士觉得可以办份小报来通知人民群众什么外国电影可以看了什么样的明星值得一追。它的初衷其实是“外国电影淘碟追星指南”。
有意思的是,这份报纸聚集起来的编辑和写手奠定了随后十年内电影媒体从业人员的基础构成样本:没一个人是专业学电影的。编辑部主任和我年岁经历都相仿,也是一位在大学法语系努力学习英语的电影迷,比我来的稍早的一位编辑的专业是会计学,另一位日剧迷转行当编辑前在旅行社做机票代理,连报社的美编也都是铁杆好莱坞迷。
曾经流行的盗版碟片
看着第一期报纸上刊出的征稿启事自荐来的各路业余写手也都很有意思,有中国最早一批日漫粉,日影专家和自学成才的电影史专家,还有一位居然是学坦克制造的。所有人当时的年纪都不超过25岁,有些还是稚气未脱的学生。但可能谁都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十年里,这伙人里出了网易娱乐频道主编、《南方周末》首席文化记者、电视电影圈的著名编剧、时光网创始人……甚至还有独立电影制片人,连手把手教我们这群门外汉报纸出版常识的编辑老师后来也成了光线创业时的副总。
我写了篇介绍奥利弗·斯通的五千字长文通过了面试。周末去了趟国家图书馆,想查查看做电影报刊到底是咋回事。埋头看了一天各类期刊报纸杂志后,我发现当时除了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环球银幕》月刊会有不少关于外国电影的报道外,还没有其他评论西方电影的出版物。我加入的可能是国内第一家关于外国电影的民营影视纸媒。
02
那个年代上网还是一件比较新奇的事儿。我去了报社才彻底学会了用调制解调器拨263上网,而且网速慢的让写稿需要资料的人急的恨不能从招待所四楼打开窗户跳下去。那时谷歌和百度还在娘胎里,雅虎搜索经常是挂一漏万,IMDb也刚成立没几年,有时候想拨号上网打开一页看几个字比现在翻墙还费劲。
编辑部获得外国电影资讯的渠道是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订阅大量的国外电影期刊。每周公共办公桌上都会堆着厚厚一摞外国电影、音乐和流行文化杂志,《综艺》《娱乐周刊》《帝国》《电影双周刊》《人物》《明星》《17岁》等等,编辑的日常工作就是从这些杂志中整理出有新闻资料性的信息,写上一整版“新闻大餐”。我还记得我在《综艺》杂志上看到哥伦比亚准备投拍李安的一部动作片“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我和编辑部主任俩人对着这条英语新闻研究了半天片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一拍大腿:这不是“卧虎藏龙”嘛?
《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片场:时为武行的张晋与章子怡套招
我开始很认真地读《电影手册》《正片》《视与听》这些带着学术意味的严肃外国电影期刊,琢磨外国作者们是怎么避免把影评写成剧情简介和观后感,而用文字还原电影的情绪并在行文中暗暗揉进写作者个人观点的。主任编辑预留了整整一版影评页面,我们用报社的公款上街买了碟放在办公室的电脑里各种研究,“家庭作业”就是每周贡献一篇千字电影评论刊登在第三版的“碟海茫茫”的影评专栏当中。
每周一的选题会,编辑部的四五个人除了上报版面内容,对着外国杂志印刷精美的图片反复欣赏选择插图和报纸封面以外,都会毫无例外地陷入对电影的争论。大家看法一致情投意合会兴奋之极,一言不合观点相左也会争得面红耳赤。
我逐渐发现写影评这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面对着同一个电影,不同的人看到的样貌有时千差万别,甚至感觉完全相反。当我试着不断转换视点的时候,会发现创作者有意和无意而隐含表达的观点,也会发现被观众有意和无意接受或忽略的信息,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对同一个文本迥然不同的观感。而评论电影的人也许并不是为了纯粹表达自己的观点,更是尝试厘清这些不同的思路对作品价值产生的影响。
创作者水平和观众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这种沟通交流中暗自存在的智力和感觉挑战;电影评论水平的高低,则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它还原了这种交流的复杂性全貌。
©Cathy Eck
这真是一段有趣的日子,可以毫无压力随心所欲不被任何人干涉地独立看电影、想电影、评论电影,还有人为此给我发工资——当然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数目,可能还抵不上现在一条豆瓣红人广播短评的价值。
03
这张小报经营了几个月以后每期销量就超过了十万。编辑部收到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大部分都是学生。
在那个互联网还没完全普及到所有城镇的年代,这份报纸给他们带去了很多关于电影的乐趣。有不止一个中学生在信里描述下课以后冲到书报亭去等报纸送到的心情,还有人用报纸的文章和图片做了很漂亮的剪报本,写上了自己的点评给我们寄过来。我们写影评的化名在信里被纷纷提起,于是便在倒数第二版“有间茶楼”栏目里用它们回答读者点名提问。
报刊亭的数量,从极盛时一座城市可分布上千座,到如今也已快要成为千禧年代的遗迹。
在北京,它汇聚来的有意思写手和作者也越来越多。经常有人没事儿就来编辑部串门,挤在狭窄的办公室里大聊特聊电影,各种热烈讨论和放声大笑的声音在空荡的招待所走廊里回荡。因为不需要坐班,编辑部里也有非常安静的时刻,我记得有一阵家里电话线出了问题没法上网,我只好每天骑车去编辑部写稿。
不是交稿日编辑部一个人都没有,我打开不知谁在电脑里下载的许美静《蔓延》MP3,一个人就着音乐噼里啪啦打键盘写影评。听着窗外初夏的蝉鸣,沐浴着下午的阳光,瞬间觉得这日子过的也太美好了,千万不要结束。
好时光总是短暂的,互联网时代突然就到来了。
1999年11月10日发行的《戏剧电影报》关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专题报道(作者供图)
报纸出了一年多,我去了趟上海写了篇上海电影节综述大稿(印象里这应该是北京媒体第一篇关于上海电影节的长篇报道),回来不久就有人拉我去一家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互联网内容公司当电影栏目主编,开出的工资是报社的十倍。其他人也都陆续去了互联网公司。又过了两三个月这份报纸自己也消失了——它被《戏剧电影报》收回,成了新出版的《北京娱乐信报》的一部分。
我由一个电影乐趣的发现者和推广者变成了提供内容的服务员。
在互联网公司我过得不太适应。除了在密闭带中央空调的高档写字楼里炼出了偏头疼的毛病,更不太喜欢领导以网民的喜好作为内容提供方向的运营策略。那时候公司内部就已经有了成熟的网站用户行为和使用习惯统计技术,公司的市场部门能精准地向特定用户群定制投放和他们当下浏览内容相关的广告。连带着,我们也必须根据计算出出的用户使用习惯制作内容。
2020年2月27日,法国电影杂志《电影手册》的大多数编辑因不满新的领导层对杂志内容的干涉而宣布集体辞职。
我由一个电影乐趣的发现者和推广者变成了提供内容的服务员。
那时候年轻,对这一转变很长时间感到非常不爽。看上去似乎为人民服务是天经地义,但具体到电影媒体这个行业,难道不应该为大家不断打开新窗口,提供新鲜甚至出点小格的视角才是更负责也更有趣的职业精神么?
这个困惑其实类似于在春节档的今天是否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就该对《唐探3》赞不绝口推崇备至。我不时想起做“落后”纸媒的时代,我们可能因为并不知道读者具体喜欢的是小李子的哪根汗毛,就自作主张在报纸上开始向他们推荐浅野忠信了,好像结果也不是那样坏,因为在信息还不对称并没有完全开放的时代(我不确信互联网是不是真的解决了“不对称”的问题),在任何一个领域稍微比别人知道的多一点的人都有责任把那些新东西告诉别人,而不是让大家像食草动物一样不断反刍自己嚼烂甚至已经排泄过一遍的食物。
彼时的《戏剧电影报》是影迷们窥视海外文明的一扇窗,也成为一批电影媒体人的训练营(作者供图)
间或着,我也去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另一些民营电影纸媒帮着做点策划,但也没找到那股在报社的干劲。21世纪初的纸媒也在变化得更接地气儿,比如我去呆过几天的一家新办媒体,在创立之初就已经决定要和某著名导演/演员捆绑在一起,不断地发吹捧他的各种文章,这几乎已经是现在电影媒体和片方携手双赢的雏形运作模式。
很多人都说,片方挣大钱、媒体挣小钱、观众笑哈哈,这难道不是皆大欢喜的和谐形势么?我左思右想觉得这已经超出了电影范畴,而演变成在抽象形而上的层面,大家是否愿意当那只坐在井底的青蛙的问题。
原来报社的同事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和新的媒体时代相恰甚欢。我挺欣赏的编辑部主任就逐渐消沉下去。他是我认识的最资深美国电影影迷,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新奇的关于电影媒介的新主意,却只能接下去在一家大型日报社里爬格子,被淹没在各种必须报道的新闻和必须写的文章里。几年以后他结婚移民加拿大,彻底离开了电影媒体行业,成了一名通讯工程师。
渐行渐远的读报时代
05
现在想起来,在报社的那段日子,我是幸运地处在了一个由纸媒转向互联网、由官方媒介转向民营媒体的短暂转型空荡期。在那之前,还没有媒体深度依赖互联网传播信息,更没有个人在私营媒体的平台上贸然写什么电影评论——当年写了也没地方发表。
互联网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点点渗透,私营电影媒体的出现,让我们这些初代电影评论个体户突然有了信息来源的渠道和发表文章的平台(这里面不但有纸媒,也有最早在西祠、新浪、网易等论坛的网络电影社区),于是出现了这一小段儿可以随心所欲独立自由评论电影的快乐日子。
但再接下去,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商业电影媒介,抑或是中国电影工业,都猛然膨胀成了身形巨大的怪物,对在其中谋生的小人物们毫无商榷余地地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信条。把这些没有固定单位去上班,也无甚其他吹拉弹唱特长,只能靠爬格子谋生的电影写手们都规训为只要听话就能活得蒸蒸日上的马前卒。
但在那个短暂的“前网络电影媒体”时代,起码是我,还曾经天真地以为这评论电影的自由时光只是刚刚开始,它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
编辑|徐元
助理编辑|Owlet
排版|Owlet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