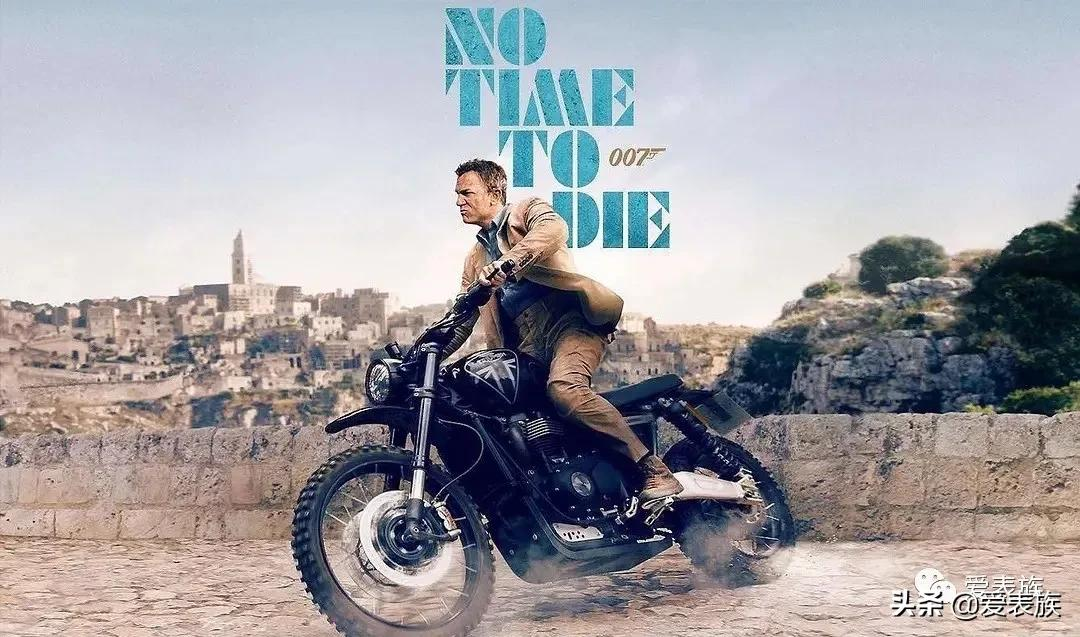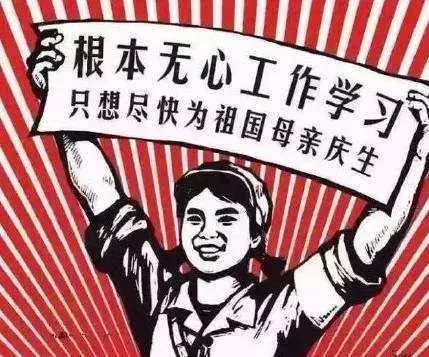邮差微电影剧情「解析」
--第7篇--
春节前夕,一则关于陈佩斯与老搭档朱时茂登上2020年春晚的消息不胫而走,多数人没敢信。毕竟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也盛传这对老搭档将合体登上央视猪年春晚,甚至具体到了小品名称,一度引发热切期待。结果,老哥俩中有微博的朱时茂当时亲自辟谣,抱憾地说:“我和佩斯真心感谢观众对我俩一如既往的喜爱和挂念。”
这一次,期待终于成真。大年初一,他们即将出现在北京台春晚,只不过角色变成了引介人,将舞台留给各自的儿子——陈大愚和朱青阳。
一转眼,距离陈佩斯、朱时茂第一次在春晚亮相,竟已过了36年。1984年春晚,这两位八一电影制片厂青年演员合作表演了《吃面条》,逗乐了全国观众,从此确立了“小品”这一电视晚会节目的新形式,自身的命运也与春晚绑在了一起。
那些年,两人创作并演出了《羊肉串》《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等雅俗共赏的春晚小品,直至1998年的第11个作品《王爷与邮差》。转过年来,两人就因央视下属公司侵权,协商无果后诉诸法律。官司胜了,但从此再没登上过央视春晚,陈佩斯更是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
在民间文学中,他被影视行业“封杀”,只能“退守荒郊种石榴”以求东山再起。实际情况是,央视不止一次邀请他“复出”春晚,可陈佩斯的创作热情已从短剧(他对小品的归类)过渡到了更自由、更完整的艺术形式。
话剧《戏台》剧照。
“消失”在荧屏的那些年,他创立的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先后打磨出了《托儿》《阳台》《老宅》《戏台》等完全面向市场的成熟话剧。2019年,《戏台》在国内开启第11轮巡回演出,陈佩斯仍作为导演和主演亲自上阵。49场下来,一路叫好叫座。
在该轮巡演的倒数第二站广东佛山,南都记者见到了年届66岁的陈佩斯。他胡髭花白,但神气平和、声音清朗,一招一式充满戏剧张力。言谈中,他流露出的对于喜剧原理和技术的思考,早已深入旁人难以想象的层面。
陈佩斯说,2020年,他和团队还是会立足剧场,除了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还要把好的作品带到小地方去:“很多地方你必须去开发它,打破过去观众坐在台下是被教育的这种观演习惯,开启他们笑的功能……把笑声还给百姓。”
在这条路上,他说自己孤独地走了大半辈子,绝不会躲避困难。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物体往前移动的时候,速度越快,它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凡是遇到困难我都会高兴,说明我在往前走,前方一定有我还不知道的东西。”
急流勇退改行话剧
时隔多年,陈佩斯已经说不出他上一次参加央视春晚的具体年份,但记得那个作品是《王爷与邮差》。当时朱时茂的麦克风掉了,靠蹭和吼演完整个节目。
陈佩斯告诉南都记者:“下了那台,我就决心不再来了,并不是后来他们说的‘打官司’什么的。”对央视春晚,他的情绪复杂,既有对知遇之情的感念,也有因创作氛围改变产生的遗憾和痛惜,后期则是拗不过各方期待的勉强和挣扎……最后,一场官司中止了一切。他反倒想说:“感谢它,让我终于从名利场退了下来。”
从春晚舞台急流勇退之后,陈佩斯并没有如传闻中那样陷入消沉,而是忙于为自己的喜剧实践寻找下一个出口。
1994年,陈佩斯注册成立了北京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起初曾涉足影视行业,留下了《孝子贤孙伺候着》《太后吉祥》等经典作品,但一直未能走通独立制作与发行之路;那时,他也考虑过与人合作,可是人家递过来的“顶好”的喜剧剧本,他根据自身经验,总能轻易地看出技术问题,双方对喜剧的认知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没办法了,我只有自己做。”最终陈佩斯决定进军剧场,做舞台喜剧,原因之一就是,当年一台话剧的制作成本仅以数十万计,他有能力承担,不用去依赖外部资本。
2001年,由大道文化自行创作、经营的首部话剧《托儿》问世,很多人持观望态度——倒不是怀疑陈佩斯的水准,而是因为国内话剧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高歌猛进之后,在世纪之交正处于低潮期。用陈佩斯自己的话说,当时即便有演出,也已经“没了买卖”,赠票或组织观演几成惯例。他却偏偏要靠作品把秩序扶正,杜绝赠票,以不低的票面价格公开售卖。
结果有目共睹,《托儿》在北京一票难求,第一轮巡演进账4000万元。演出行业震惊,陈佩斯本人却不意外。他对南都记者解释:“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小品、短剧演出之后是什么样的效果。现在我又成长了好几步,拿出了一个完全成熟的戏剧,(市场反响)真的都在预期当中。”
对儿子“接班”不担心
沿着《托儿》开辟的新路径,其后陈佩斯的大道文化又推出了《阳台》《阿斗》《雷人晚餐》《老宅》《春宵保卫战》《戏台》等结构精致、同时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舞台喜剧,从出品到运作模式,都令人想到美国的百老汇,却更具平民立场。另一边,陈佩斯开始着手稀缺喜剧人才的培养,于2012年启动了首届“喜剧创演训练营”,面向全社会招募学员,而不用曲艺界严格的“师徒制”。
正是在那一年,陈佩斯之子、生于1990年的陈大愚开始随父亲从事喜剧。“他自己要求、自己报名的!”陈佩斯笑着说。此前,陈大愚选了一个理科专业,在美国深造,学着学着才发觉自己真正的兴趣,于是了结了国外的学业,报名成为大道喜剧训练营的首批学员。
对自己儿子,陈佩斯说:“我也不是乐见其成。我也得看他成还是不成。一开始糟糕极了,同样没基础,他比起同一期的孩子们差一大块儿。可是其他人毕业之后,能上电影、电视,演演儿童剧,演演别人的话剧,他跑不掉。因为他是我儿子,他必须得替我扛一点儿这个担子。扛着扛着,在这里头浸的时间长了,戏就越演越精了,慢慢地就有自己的东西生成了。”
这次陈大愚登上北京台春晚,对不少电视观众来说是一次“亮相”,其实他已经30岁,在话剧舞台上历练已久。2013年,他就接棒父亲,挑大梁主演了《托儿》青春版;曾因改编并执导话剧《春宵保卫战》获得首届北京戏剧新势力“潜质创作人”奖,并担任了2017版《阳台》和2019版《托儿》的复排导演。
陈佩斯评价道:“他不可能全盘接受我的东西,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东西。对他,我不担心、不着急——好多事情该怎么着,就会怎么着。所以别为别人着急,也别为自己着急。”
曾受卓别林深刻影响
活了大半辈子,陈佩斯心里想的仍是喜剧。用他的话说,“我自己不是假喜欢,是真喜欢;老天又给我‘摁’到这儿了。幸福感就在这里。”
陈强。
陈佩斯对南都记者回忆,他对喜剧的理解最初源自父亲陈强。身为“新中国22大影星”之一,陈强曾饰演过《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教育观众何为旧社会地主盘剥劳苦大众的“阶级仇恨”。但也就是这位老共产党员,在上世纪70年代末忽然转型搞喜剧,他想让中国的老百姓忘记仇恨、找回笑的能力。
陈佩斯是家中的二儿子,他生于1954年,15岁赴内蒙古参加生产建设兵团,返城之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做配角演员。陈强手把手地带他演喜剧。1979年,父子俩合作的喜剧片《瞧这一家子》公映,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差不多在同时,陈佩斯开始接触卓别林的默片,还在《电影艺术》杂志上读到了卓别林讲喜剧的文章。其中写道,笑的产生是源于“窘境”。这对陈佩斯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是我往核心方向走的第一步。”如今,这位中国的喜剧大师如是评价。但他在后来的创作中逐渐发现,“窘境”这个翻译方式并不准确,它在中文语境中更强调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却让人忽略了主角置身且无法逃脱的那个时空背景——譬如卓别林,他的默片就永远围绕着大工业时代的底层贫民。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起,陈佩斯的小品和影视短剧(很接近现在的“微电影”)就格外注重客观条件的设置,他认为必须是在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用人和道具去结构故事,并将矛盾的起因埋藏在人物设定之内。“就像老话说的,‘扎在肉里的刺儿,你怎么动都疼’,故事就好看。”
“喜剧的内核是悲情”
陈佩斯有一个著名观点:喜剧的内核是悲情。
“其实‘悲情’也不是很准确,只是一种比较文学化的表达。”陈佩斯告诉南都记者,“我想说的是,所有能让你‘扑哧就乐’的这种笑点的产生,一定是被观看者有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剧烈程度、被观看者的痛苦程度,决定了你笑的程度。”而戏剧的妙处就在于,可以虚拟一种具体的困境,演员沉浸其中,将角色的痛苦展现出来,观众就会快乐,“这是一种人类的智慧。”
创作于2015年的话剧《戏台》,是陈佩斯喜剧理念的一次充分展示。它讲的是民国年间,一个京剧戏班在军阀、政客、黑帮和梨园行名角儿之间左支右绌、为保小命不断妥协的故事。2019年的全国巡演中,65岁的陈佩斯仍是那个苦命的“侯班主”,他在台上最常做的就是抱头蹲着,眼神惊惶地观望各种不速之客,站也是歪着站,从未挺直腰杆过。细腻生动的窘态,令观众频频爆笑。
尽管陈佩斯承认,早几年从老友毓钺手里拿到剧本、写导演阐述的时候,自己经常对“侯班主”的境遇产生同感,但《戏台》归根结底不是“言志”的作品。他说:“我在台上只是一个艺人,在排练当中是导演,一切都是按照喜剧的规律去走。只不过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我尽可能把它的分量做得厚一些。”
在快手、抖音等移动媒体普及的当下,陈佩斯仍据守舞台,追求以120分钟左右的时长展现更深厚、复杂的喜剧,心疼他的观众觉得,这简直是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相比起曾让他一夜成名的电视来说,也太慢了。可是陈佩斯觉得,“我一场一场地演,他们一张一张地买票支持,戏一场一场地调整、完善”,这是一种非常平衡、舒适的心理过程。
用《戏台》的一句话就是:“谢谢您抬举,咱们台上伺候!”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部分资料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