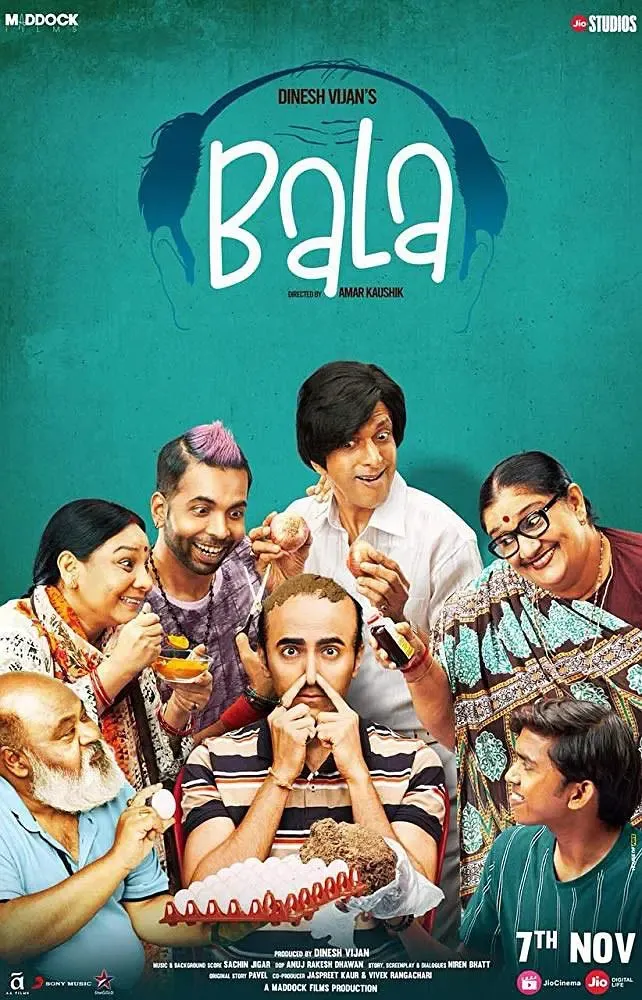恶作剧(小说)-今日头条
王 威
没错,恶作剧是个人名字,而且是个女人的名字。
我跟恶作剧相识,源于一场车祸。
那天,我开着阿水留下的车去帮人鉴定古董。 我对古董略懂一二,并且替阿水经营古董店三年了,可是经营并不成功。 自从阿水三年前不声不响地出走以后,店里的生意就一落千丈,我不得不靠给人家鉴别古董混碗饭吃。
车子刚驶进市区,我前面那辆绿色牧马人就被后面的车猛烈追尾,撞上了路中央的隔离桩……我吓得忘记闭眼睛,只是狠命踩着刹车,眼睁睁地看着它在我眼前干瘪报废。
我虽然叫刘威风,可实际上一点也不威风,阿水跟我大声说句话,我都会缩起脖子来。 阿水就骂自己,怎么会看上我这么个草包男人。 说实话,阿水走后,我的胆子变得更小了,我怕出现什么意外没人替我扛。
我旁边的车子一辆接一辆小心翼翼绕过这个倒霉现场,一溜烟跑了,只有我还死命踩着刹车停在那里。 我擦了擦顺着脸颊流下来的冷汗,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还不走,是因为腿一直发抖找不到油门吗? 直到牧马人的司机下来,我才明白,原来我想看看司机是谁。 阿水走时也开着一辆同颜色的牧马人。
牧马人的司机就是恶作剧。 当时她戴着一副墨镜,腆着大肚子,一副孕妇的形象朝我的车子走来,那副气宇轩昂的架势仿若阿水。 我缩了缩脖子,隔着挡风玻璃,我忽然发现有血顺着她白色的裤管往外流……她几乎是一步一个血脚印走来。 我彻底慌了,赶紧低下头装作找东西的样子在车里乱翻……车门被拉开,恶作剧坐到了车后座上。
恶作剧的话没有丝毫温度,她说,去妇幼保健院。 我似乎听到了汩汩流血的声音,头皮一炸,车子用光的速度飞出去……
我跟恶作剧就是用这种“血腥”的方式开启的初见。 在医院里,护士质疑她的名字,她见惯不怪地甩出身份证,我伸长脖子从她肩膀上方看到身份证上“恶作剧”三个字。 她回头瞪了我一眼,我赶紧缩回脖子。
恶作剧在医院里待了半个月就出院了,出院时她的肚子憋下去,恢复成了一个窈窕淑女的模样。 对于失去的孩子,她并没有多少悲伤,相反好像还有着隐隐的兴奋。 我不想揣测她的生活,因为这个城市多的是这种视生命如儿戏的男人女人。
恶作剧用车祸赔偿的钱买了两瓶茅台。 她拎着来找我时,我正在店里给人家鉴别古董,她坐在旁边很安静地等我。 我偷眼看了她几次,从外表看,她跟那些高档写字楼里出来的女孩没有什么不同,干脆利索,优雅漂亮,走在路上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最后一眼,正好碰上她的目光,我的眼神赶紧缩回来。
吃饭的时候,她鄙视地说,叫啥刘威风,你干脆叫刘缩头算了,看看你那熊样! 我没吭声,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忍。 比如来店里看货的那些人,不管他们对我的古董挑剔得多么可笑无理,我都能消化掉,不跟他们分辨,尤其阿水不在的日子。 多数时候,他们就觉得一拳拳打在软棉花上,毫无成就感,也就没有兴趣再进来了。
这晚,在古董店的阁楼上,恶作剧喝醉了。 开始喝的时候,她还郑重承诺,今晚保准不喝醉。 喝到一半,她把高跟鞋朝天棚扔去,说如果高跟鞋掉下来,说明小米粒她爹是爱她的,如果掉不下来,说明小米粒的爹对她是虚情假意。 任谁都明白,她的这个心愿就是自我欺骗,扔到半空中的鞋子怎么会掉不下来呢? 地球又没有失去引力。 我预防鞋子掉下来砸到我的脑袋,提前抱住了它。
鞋子扔上去以后,屋子里没有一点动静。 我跟恶作剧变成了两个活生生的剪影,她仰脸看天棚,我抱头瞅地板。 桌子上的茅台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像扔鞋子以前的这个夜晚一样美好。 出乎剪影们的预料,鞋子没有掉下来,它“刺”的一声,尖锐的鞋跟笔直地插进塑料天棚里,像一根茄子那样挂在上面,幸灾乐祸地俯视我们。
看到恶作剧的瞳孔在急剧放大,我想把茅台藏起来,可是晚了。 她一把把酒瓶抢过去,笑嘻嘻地说,大威(我就是从这里开始对她产生了不可抑制的信任感,因为我妈活着时也叫我大威),她说,大威,这两瓶茅台一共花了我五万块钱,你看看年份。 我没看,只是从心底怜悯起妈妈,五万块钱够我当清洁工的妈妈绕地球扫一圈了。
我说,小恶,我们还是吃点菜吧,喝这么贵的酒还作践身子,可惜了。 我也不知道是可惜了酒还是身子。 恶作剧大笑起来,边笑边擦眼泪宣布,你就是个二货!
恶作剧酒量很大,第一瓶茅台见底以后,她还保持着清醒。 我给她做了一碗酸辣汤,以前阿水在的时候,就爱喝我做的酸辣汤,她说喝了以后有醍醐灌顶的功效。 我不希望恶作剧在我这儿喝醉,女人喝醉了很麻烦。 如果阿水在就好了,我抑郁地想。
恶作剧看了一眼酸辣汤说,你不会下毒吧? 我点上一根烟,席地而坐,不再理她。
恶作剧边喝酒边说她和小米粒爹的故事,说着说着,我恍惚觉得小米粒并没有被恶作剧流产,而是活了下来,正坐在天棚的高跟鞋里荡秋千。 我抬头寻找高跟鞋,烟雾缭绕,什么也没看到。
我对恶作剧说,你跟小米粒的爹还好吧? 恶作剧奇怪地看着我说,不好能怀孕吗? 十年了,这是他治疗弱精后我第一次怀孕。 恶作剧喝了一口酒,朝我笑了笑说,可是,小米粒没留下我很开心。 我快速眨巴眼睛,想把她的话串联起来,确定她是不是流产把脑子搞出了毛病。
墙上的时针指向九点,我开始犯困。 可恶作剧面带春色,又开了另一瓶茅台。 晚上一到九点我就犯困,这是阿水在时给我养成的习惯。 更何况今晚我还喝了两口茅台,眼皮就跟被胶水粘住了一样睁不开。
在我睡着之前,我好像听到恶作剧在跟我说她小时候的事情,她说她那时不想练钢琴,被妈妈用炒勺把额头打出了一个坑。 她伸过头来让我看头上的坑,我迷迷糊糊地应付了她两句。 鬼知道我接下来为什么还要用手去摸那个坑,大概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睡意,她毕竟第一次来店里做客,总不好表现得迷迷糊糊。 恶作剧顺势抱住我的手臂哭起来。
我强忍睡意说,阿水,不要哭,会好起来的。 三年前,阿水在我怀里哭,我就是这么跟她说的。 阿水说,可是晚了呀。 当时我没有听出她话里的意思,我拍了拍她说,只要有信心,一百岁也不晚。 其实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哭什么“晚了”。 第二天我起来,发现阿水把古董店和一封信留下,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 别问我那封信写了啥,我也不知道,因为没等我看,信就被打翻的茶水浸染得面目全非。 在太阳下晒干以后,它就变成一封“信干”,字迹再也无从辨认。
我怕自己一觉醒来看不到“阿水”,所以尽力让自己清醒过来。 我抓住恶作剧的手腕让自己坐正,四下张望了一会儿,一切还是老样子,我断定刚才做了一个有阿水的美梦。 可恶作剧忽然问我,阿水是你女朋友? 我一个激灵,你认识她? 刚问完,我才觉出自己傻。 恶作剧笑得喘不过气来。
恶作剧问我,你爱阿水吗? 我想也不想就点头,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以外,还有谁能像她那样百般护着我。 恶作剧说,想不想知道她爱你不? 我说她爱我。 恶作剧不屑地瞅我一眼说,换个说法,想不想让她回来? 我盯着她使劲点头。
恶作剧问我们的古董店以前生意怎样? 一提以前的古董店,我就来劲,我两眼发光,刚要大肆渲染一下阿水在时店里的辉煌,被恶作剧打断了。 她说,我只负责她回来,不负责她回来的后果。 不能讲讲阿水在时的古董店,让我有点沮丧。 我说什么好后果坏后果的,最好的后果是结婚,最坏的后果是她再次消失。 看到我不耐烦的样子,恶作剧说,你这样想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只有遇见事情才能检验爱情。 我说我不检验爱情,我希望阿水回来。
恶作剧冷笑地着看我,一点也不像刚做完流产的女人,倒像是个高高在上的神,让我有些自卑。 阿水从不这样对待我,她总是用简洁的语言告诉我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不用我费心去猜。
恶作剧喝了一口酒,神色有些悲戚,仿佛想起了什么不该想的事。 没等我开口,她就开始给我设置“剧本”:她让我通知阿水,说自己被公安、法院或者什么人盯上了,希望她回来捞自己。 我笑着说她也不会信啊,你看看,我这样的是敢去抢劫还是敢去杀人? 恶作剧看了一眼楼下店铺说,那就说虚开增值税发票。
我惊愕地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阿水父亲去世以后的两年,阿水把古董店经营的日进斗金。 那时钞票多得让人乏味,她就把它们铺在阁楼上当地毯踩来踩去。 有一次我们坐在这些钞票毯上喝果汁看电视,看到电视上正在宣判偷税的案子,阿水神秘地告诉我,她之所以有这么多钱,就是因为虚开发票。 我对这些一点不懂,只能懵懂地看着她。 她说,出事后你替我去坐牢啊。 听到这里我笑了,继续喝果汁,因为我知道即使真出事,阿水也不会让我去顶着的。 看到我的笑容,阿水的眼睛里略过一丝黯然。
我慌乱的样子,引得恶作剧不怀好意地打量我,你他娘的不会真虚开过发票吧? 我连连点头,哀怨地看着她。 这一瞬间,我真把她当成了高高在上的神,想跟她忏悔,可是除了说出阿水的名字,其他我什么也不知道。 恶作剧说,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样!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她朝我诡异地笑了笑。
微博私信给阿水以后,我不确定她会不会看到,因为,这个微博她已经好多年不用了。 开始的几天,我还会天天上微博看看有没有阿水的回音,时间一长我松懈下来,甚至感觉自己有些傻。
半个月早就过去了,就在我把这件事彻底忘掉后的某个清早,睡眼惺忪地开古董店的门,随着卷帘门的上升,阿水像一帧仕女图出现在门框里。 我的脑海里一瞬间空白了。
阿水比走时更瘦了,像个人干。 没有废话,人干开口直奔主题,发票出事了? 我心里一喜,恶作剧真***的神算。 我刚想摇头,想起恶作剧叮嘱的,想要留住她,就要照“剧本”上说的去演。 我赶紧点头。 阿水走进店里,四下看了看说,哪来的钱喝茅台?
我使劲吸了吸鼻子,这么长时间了,酒味还没有散尽? 我心虚地看她,阿水也正在看我,眼睛水汪汪的,像我老家的湖水,碧绿幽深,我想一头扎进去。 于是我就把她揽过来,一头扎进她的怀里。 阿水身子明显一软,于是,我们俩汇合成一汪水,楼上楼下流淌环绕……
从床上起来,阿水照例赤脚光腿去拿果汁,边喝边问我发票的事情。 我照着恶作剧教得一字不漏地说了一遍,她以前虚开的发票,经侦大队过来调查了。 阿水面无表情地说,我把流程写下来,提审你时,你照着说就行。 我心里一沉,迷茫地看着她,怎么会这样? 难道她也在照着恶作剧的剧本演? 阿水放下果汁盒子,开始在桌子上写。
昏黄的光线透进来,打在阿水年轻光滑的身体上,勾勒出的曲线让我伤感。 那晚我跟恶作剧信誓旦旦地说,阿水不会跟她说的那样,她会替我挡着一切,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更何况发票的事是她做的,她肯定不会让我去当替罪羊。 恶作剧没有跟我辩解,只是嘴角一弯,一副看傻瓜的表情。
阿水递给我那张写满字的纸,完全没有内疚或者悔恨这些表情,一副轻松的样子。 也许她不知道发票的严重性? 我打算提醒她一下,这也是恶作剧的剧本设定内容。 没等我开口,阿水盯着我严肃地“宣判”,依照税额,你会被判五至十年。 我的腿发软头晕眩,极想就地坐下,可为了保持最后的尊严,我一步一步沿着扶梯开始下楼。
晚饭时,我拿出恶作剧上次剩下的茅台全部喝光了。 喝醉的感觉很愉快,我跟阿水说我们的童年,说恶作剧的车祸,总之说了许多感性的话,阿水被我说哭了,我也把自己说哭了。 我们抱头哭的时间很长,以至于哭完以后都忘记了为什么哭。
阿水并没有被我这些感性的语言和泪水所打动,临睡前,她嘱咐我把那张写满字的纸背熟,否则提审时会出纰漏。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阿水推醒我说,我要走了。 我没问她要去哪里,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的脑海里盘旋着恶作剧给我设定的后面的台词。
阿水对于我的恍惚有些不忍心,吃早餐时,她安慰我说,不要怕,提审没事的,数额实话实说就行。 只是数额实话实说吗? 我低头剥着鸡蛋装作轻描淡写地说。
阿水的筷子一抖,夹着的小菜掉在桌子上。 你想把我供出来吗? 阿水停顿一下,重新夹起小菜放进嘴里,边咀嚼边看着我。 我的心里充满浩荡的酸痛,不管阿水会不会离开,我们都再也回不去了。
从早饭后,阿水就不再说话,她站在窗前呆呆地望着外面,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如果换作以前,我会上前抱住她逗她开心。 可是现在我握着那张试图把我送进监狱的纸,怎么也迈不开腿。
大威,你在怪我吗? 阿水没有回头,说这话的时候嗓音暗哑。 阿水的话一出口,我感觉心里像开了天窗,不再憋闷。 如果阿水以前这样问我,我会赶紧否认。 可是现在有剧本,我很乐意照着背下来,看看以后的剧情。 我说,是的。 阿水很吃惊我这么直白,她回身盯着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问我,恶作剧经常来吗? 这个问题出乎我的预料,我有点慌乱,结结巴巴地说,没有,就来过一次。
你们玩得开心吗? 我不知道阿水的话什么意思,没有敢接下去,因为女人有时很复杂,她们擅长指东打西。 可阿水在等着我回答,我只得模棱两可地说,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就是玩呗。 阿水说,你们是怎样把高跟鞋嗨到天棚上去的? 我猛然抬头,看到匕首般插在天棚上的高跟鞋。 我的眼睛又开始极速眨巴,我控制不了。 恶作剧那天是穿什么走的呢? 我一直以为她把鞋子弄下来了。
阿水没有等我回答又转移了话题,她说,你替我坐牢感觉很委屈吗? 我想说是的,我还想说,原来你没有我想的那样爱我。 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恶作剧总结这场戏的时候说过,爱情就是生病,灾难是治愈它的良药。 果然,灾难刚一露头,这场爱情就在考虑痊愈,彼此抛弃。
我说,阿水,你今天就走吗? 阿水摇摇头说,不走了。 对于阿水的这个决定,我并没有出现以前预期的那样惊喜,我甚至有些厌烦起来。 我借口去开卷帘门,离开了。
这一天跟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店里没有一个顾客。 我推掉两个古董鉴别的邀约,坐在柜台后面,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影子有些恍惚。 妈妈去世前,躺在床上指着我身前身后说,怎么进来的都是影子呀,你姥姥,你奶奶、你太奶奶……妈妈握了一辈子大扫帚的手指弯曲苍老,像树根,我惊恐地握住这些树根,让她不要吓唬我。 妈妈反手握住我的手,心疼地说,大威,别怕,找个疼自己的人。
想到这儿,我明白自己恍惚的原因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阿水就是妈妈嘴里说的那个疼我的人,到现在我才看懂,她不是。 多亏恶作剧。 想到这儿,我想给恶作剧打个电话,告诉她我要离开这里,永远不回来了。 可是想到阿水在阁楼上,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还是见面说吧。
万万没想到,阿水跟我想到一块去了,她下楼跟我说,给恶作剧打个电话,我想跟她见面。 我条件反射般反对,你想干什么? 我的激烈没让阿水意外,她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想谢谢她,让我知道我们的爱情病了。 我沉默下来。 即使我现在说出来这是恶作剧一手导演的戏,目的是我想让她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还没打电话,恶作剧来了。 恶作剧来得很狼狈,居然是拖着一个行李箱匆匆跑进来的。 刚一进门,她就说,大威,我要借住几天。 然后她看到了阿水。 恶作剧的角色转换得很快,不愧是经历过风浪的人。 她说,阿水回来了? 她熟稔的口吻让我产生了错觉,以为她们以前就认识。 阿水点点头说,住几天? 恶作剧没有回答,而是说,大威,给我把行李拿楼上去,别放这儿碍事。 我没敢看阿水,拎起恶作剧的行李几步跑上阁楼。 阿水的眼睛锥子般盯住我的后背,我觉得后背一片灼热。
我下楼的时候,恶作剧和阿水正一人一盒果汁,喝得心平气和。 女人就是这样口是心非,明明心里愁肠十八弯,表面上还能比赛谁比谁更冷静。
下楼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恶作剧的脚,她穿了一双鞋跟更高的鞋子。 看到我下来,她笑嘻嘻地说,我宣布一下,我是被小米粒爹追杀逃难来的。 我心里一惊,脑海里立即跑进来一个手举菜刀的男人。
阿水吩咐我去买一瓶白酒,如果能买得起茅台更好,她边说边用眼睛瞟了一下恶作剧。 恶作剧没有接茬,她把手里的果汁盒子捏扁又弄圆,反反复复,在思忖什么。
晚饭很丰盛,除了白酒,还有半只白斩鸡和一条鱼。 可是酒喝得底朝天了,白斩鸡和鱼都没有动一下。 反倒是恶作剧和阿水成了好朋友,她们醉醺醺地勾肩搭背,仿佛刚刚想起来她们是结伴投胎到这个世界上的好姐妹。 阿水也知道了恶作剧、小米粒和小米粒爹的故事。 阿水的舌头都不打弯,也没有忘记问恶作剧为什么不想留下小米粒。 恶作剧笑了,恶作剧笑起来很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笑让我悲伤。
恶作剧说,她跟小米粒的爹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在恶作剧的主导下,开了一家电子公司。 这些,恶作剧上次一个字都没跟我说,我还以为恶作剧是小米粒爹包养的小三呢,原来小米粒的爹是个吃软饭的,我咧了咧嘴。
阿水说,原来他跟大威一样,都得指望女人。 恶作剧和阿水一同怜悯地看向我,在她们含笑的注视下,我拿出前天医生给我开的抗抑郁的药,干咽了下去,我实在找不到东西来缓解我的困窘。
恶作剧问阿水,大威这次如果被判刑,你会等他吗? 阿水说不知道。 小米粒的爹会等你吗? 我反问恶作剧,我忽然有些厌烦她,她的出现打乱了我的生活。 在她之前,我跟阿水是美好的爱情,她的出现,让我们的爱情变成了臭狗屎。
恶作剧没有被我难倒,她说,小米粒的爹等着我,并且就如同你们看到的,他现在正在四下找我逼婚。 我和阿水同时瞪大眼睛。 恶作剧很满意自己制造的气氛,她说,我不跟他结婚,我要让他一辈子欠我的。 说完,恶作剧又开始脱鞋,我怕天棚变得千疮百孔,赶忙上前按住了她的手。
阿水对恶作剧说,他欠你什么? 恶作剧捧着自己的高跟鞋乐呵呵地说,他虚开发票事发,不敢承担责任,我替他去坐的牢,三年! 恶作剧笑着举起纤细透明的三根手指,仿佛在宣誓。 我跌坐到地板上。 我终于明白恶作剧给我设计的剧本是有原型的。 想明白这个,抑郁溢满我的心,变成泪水源源不断涌上来。 我嚎啕大哭,边哭边想靠近恶作剧,我觉得我们俩同病相怜,我们在爱情这场大病中正走向痊愈……
阿水鄙夷地看着我,让我滚远点。 我拿出藏在怀里的药威胁她说,我要全部吃了它,没法再去接受审问,警察来只能抓你! 阿水冷笑着说,你就是死,罪名也在你头上,因为这个店的法人早就改成你了。 我绝望地问她,为什么? 我想不通,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阿水冷静地说,我从来没有变过。 恶作剧闭着眼睛,眼泪纵横,可是小米粒的爹为什么变了呀? 他为什么让我去顶罪? 他不是爱我的吗? 那是因为你逞能让爱情错位了,阿水说,不管怎样,我还是相信爱情。 最后这句,我跟恶作剧都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因为很假。
屋子里寂静得如同世界末日。 这时我才听到外面落雪的声音。 妈妈就是在一个飘雪的中午离世的,那天的大雪也是这样在空中撕撕扯扯。 妈妈面带欢欣和羞涩,她说,让你爸爸等了这么久,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
我问恶作剧,为什么不跟小米粒的爹结婚?
你会跟阿水结婚吗?
那为什么要怀他的孩子?
为了流产。 为了流掉他的命! 恶作剧说着笑起来,笑得泪流满面。
阿水开始往嘴里竖啤酒,她喜欢这样喝啤酒,像个男人一样。
恶作剧去了哪儿,怎样走的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醒来,整个店里只剩下我和阿水,恶作剧的痕迹一点都没有留下。 如果不是天棚上插着的那只高跟鞋,我会以为恶作剧的出现只是个臆想。
阿水没有走,她留在店里,我们再也没有恢复以前的样子。 白天,她把做好的汤圆端给我,然后坐在楼下的柜台里,背后是落满灰尘的古董架子。 晚上,我们依旧躺在一张床上,可是中间隔得很宽。
直到高跟鞋掉下来,我们才有了唯一的一次交流。 那天,我刚端起汤圆碗,我记不清阿水回来以后,我除了汤圆还吃过别的什么。 鞋子像一个丧心病狂的歹徒,呼啸着朝我的头顶刺来。 阿水把我推向一边,她的脸颊被尖锐的鞋跟划开一道口子。
看着毁容的阿水,我问她,为什么要替我挡高跟鞋。 她说是本能。 我迟疑着问她,那为什么想让我去坐牢? 阿水的嘴角挂上一丝微笑,她转身同情地看着我说,警察来找过你没有? 我摇摇头说,于我来说,那本来就是场戏。 可是对你来说,那不是戏,你真的干过! 我开始嘶吼,我很委屈。 阿水脸上的笑容像水一样蔓延开来,我根本没有虚开过发票,看到微博上你的私信,想跟你搞个恶作剧而已,谁知道你会真以为我干过! 阿水平静地说。 看到她如圣母般光洁的面庞,我的内心充满恐惧和绝望,生平第一次声嘶力竭地怒喊,你***的在玩我啊!
阿水盯着斜躺在地板上的高跟鞋,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我喊累了,颓然坐在地板上。 屋子里很安静。 我希望阿水像从前那样,安慰我一下,告诉我恶作剧结束了,我们从头开始。 可是阿水朝门外走去。
那封“信干”的内容是什么? 我惊慌失措地朝她喊。 我不知道该如何挽留住她,忽然想起三年前她走时留给我的那封信。
是爱情,可惜被你染花了风干了。
阿水把古董店盘给我走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