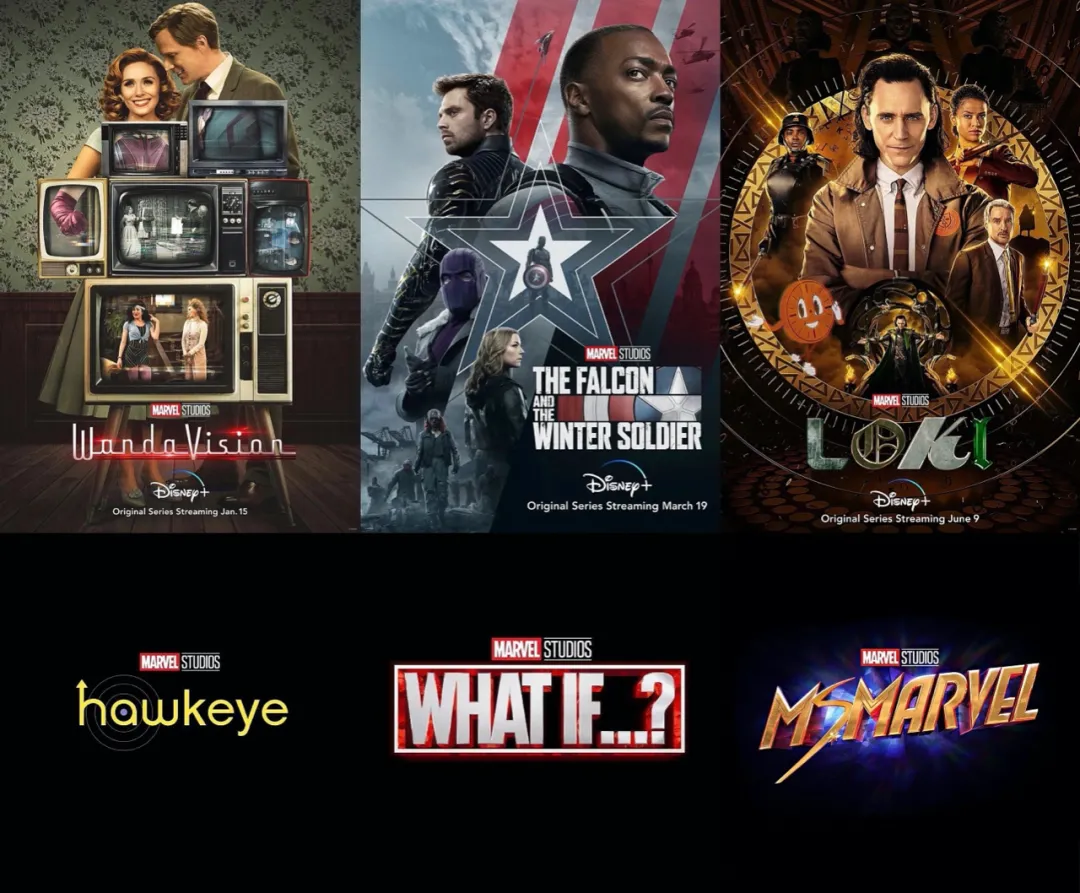莫里哀电影剧情解析「解析」
1622年,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在巴黎出生,其父是法兰西王室的室内陈设制造商。少年时,波克兰就读于当时赫赫有名的巴黎克莱蒙中学,接受贵族精英式的古典教育,阅读了不少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作品,尤其痴迷于卢克莱修的教诲诗和古罗马戏剧诗人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喜剧,这一癖好很可能与他经常在课余时间溜到巴黎小剧院看戏有关。
中学毕业后,波克兰没有依从父亲希望他接任“法兰西国王陛下侍从”封号的愿望,在首相黎塞留积极备战进攻西班牙那年(1642),年仅20岁的波克兰离开优渥的家庭,与几位喜剧艺人一起组建光耀剧团(L'IllustreThéâtre),此后带领剧团在外省闯荡十三年。
1658年,35岁的波克兰以“莫里哀”之名重返巴黎,并以《多情的医生》一剧在法国戏剧界崭露头角,这是他为法王路易十四演出的第一部喜剧。后来,剧团更名为莫里哀剧团,从此,法国戏剧界迎来了莫里哀的喜剧时代。莫里哀没有预料到,后人会将自己奉为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员与喜剧诗人,他从诞辰至今已400年,在此期间百年声名不坠且争议不断,似乎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都有重读莫里哀的必要。
1663年,路易十四亲揽朝政仅两年给两岁的王储写下了《给道芬的训言》:“一个法兰西的王子或国王,应该在戏剧娱乐中看到表演以外的其他东西。子民在演出中尽享其乐……通过此举我们控制他们的思想,抓住他们的心,有时这会比奖赏和恩惠更有效;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些看似多余的消耗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不同凡响的印象,那便是辉煌、强盛、富丽和宏大。”
路易十四亲政后,一直励精图新,致力于实现上几代法国君主的抱负和梦想:“在法国建立一个让欧洲肃然起敬的绝对君主制”。他牢牢地记住了教父——摄政主教马扎然(J.Mazarin,1602-1661)的临终嘱咐:“国王要统治一切”。通过对内削贵和对外战争,年轻的路易终于成为17世纪西欧最强势的君主,法国呈现出文艺繁荣的局面,戏剧尤为突出。
其实,迟至16世纪末,法国戏剧仍然不成气候,占据舞台的是意大利小丑剧,文人完全没有参与戏剧演出和剧本的编剧。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1585-1642)摄政后,为了给法兰西王国新政铺平道路,他看中了戏剧的政治教化功用,开始着手治理文艺乱象。1635年,身为首相的黎塞留下令成立法兰西学院,规定古典主义戏剧原则为法国戏剧的国家文艺原则,指令法兰西学院按此原则指导法国的戏剧创作。为了推进新古典主义戏剧的发展,黎塞留还下令修建玛雷剧院。
大名鼎鼎的古典主义悲剧之父高乃依(1606-1684)的好些剧作,也是黎塞留的授意。玛雷剧院建成后,首场演出便是高乃依的喜剧《梅里特》。由此可见,在国家政治转型进程中,戏剧扮演着相当重要的政治角色,或者说,法国在近代崛起时,治国者极为重视掌控文艺创作的领导权。我们知道,在路易十四时代,巴黎成了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但却没有注意到,如此文艺繁荣是法国绝对君主制的体现。
在王权政制治下,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繁荣首先见于悲剧。按伏尔泰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中的说法,马扎然主教摄政时期:当法国喜剧及至莫里哀的手里,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才臻于成熟。据统计,路易十四宫廷上演的戏剧多达数百场,国王本人尤其爱看莫里哀的喜剧,还曾打算出演剧中角色,甚至把莫里哀剧团从王弟手中强行收归自己的名下。
像路易十四这样热衷舞蹈和戏剧的国王实不多见。在教父马扎然精心教育下,路易十四懂得,国家转型期亟需戏剧整合国民的精神秩序,为一个强大的法兰西陶铸崭新的精神品质。
路易十四从莫里哀的剧作中觉察到,喜剧的特质颇为契合国家转型期打击封建势力的需要,喜剧的主角不是古代英雄豪杰或王候将相,而是,各色受到嘲笑的低劣灵魂,从而,喜剧能对现实政治迅速做出反应。古希腊的雅典谐剧让法国的古典戏剧家懂得,有品质的喜剧以与悲剧相反的方式来医治世人灵魂中的政治“病”,促使观众通过观察和审视剧中人物的可笑来反省自身。
路易十四深谙术治,他对戏剧的热爱并非仅仅是个人兴趣,毋宁说,这位法兰西君主重视戏剧,与其治国理念相关。因此,路易十四在《给道芬的训言》中写到,戏剧演出对内可塑造民众,对外能威慑外敌。可见,这位君主懂得,戏剧演出具有塑造理想的国家形象和民众楷模的政治作用,而这种认识又来自他所受过的古典教育。
公元前六世纪末,雅典政治家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os)为了让雅典成为“大国”,在雅典城邦设立了狄奥尼索斯戏剧节,把民俗式的表演变成了城邦戏剧。今人大多仅仅看到雅典戏剧的繁荣,却很少注意到戏剧繁荣与政治家庇西特拉图的王者用心相关。
正是由于看到戏剧演出对于城邦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在雅典民主政治的鼎盛时期,伯利克里(前495-429)为了鼓励民众看戏,开始实行“观剧津贴”,他本人也是个戏剧迷,与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私交甚笃。
此外,柏拉图的好些对话作品都具有谐剧形式。尤其应该注意到,在《会饮》这部哲学谐剧中,苏格拉底的女教师狄俄提玛将制作音乐与制作法律同样视为爱欲的高级形式,她不仅将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称为“诗作”,也把吕库戈斯和梭伦的立法视为“诗作”。
这意味着,戏剧制作与法律创制同属人世中最高的制作,前者为灵魂秩序立法,后者为政治秩序立法。灵魂与城邦的正义与否和有序与否,端赖谁是高明的制作者。
据说,被称为“哲人王”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年少时狂热地迷恋法国戏剧,羡慕法兰西的文化共同体。为了模仿法兰西,未来的普鲁士国王他甚至违背父亲的旨意,执意学习拉丁语,这位王子的脑子里充满了自然神论派哲学家的思想。不过,这位少年天子相当清楚身为王者的责任,在一本用法文撰写的论政府原理的书中,弗里德里希二世说:王候之于其所统治的国家,是和头之于人一样;他的责任是在于为整个的社会而视察、思维和行动,谋取社会所能得到的一切的利益。
其实,直到16岁的法王路易十四亲政的1654年,法国人的读写能力仍然极其低下。根据19世纪一份关于法国人的读写能力调查报告来看,16-17世纪时法国人的读写能力极弱,比如在法国东部,只有一半地区,会写自己的名字的男子达到70%,女子却只有30%。就全国而言,直到17世纪末,女子中会写自己名字的才占14%。
因而,对于普通民众施行教育的最好工具莫过于戏剧演出。一方面是看戏的知识门槛低,目不识丁的观众也能进戏院看戏;另一方面戏剧演出对民众教育起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
于是,自17世纪30年代起,法兰西在雄心勃勃的首相黎塞留的极力倡导之下,文人创作的戏剧演出终于登上大雅之堂,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前在法兰西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意大利的小丑戏,如今在首相的管制之下,表演才开始成为一种正式职业。
黎塞留致力于“广开言路”,他笃定要赢得公共舆论的主导权。对于17世纪的法兰西而言,国家正从神权政制走向绝对君主制,为了对抗教会的力量,终结宗教导致的政治共同体的内在分裂。对黎塞留而言,主导法兰西舞台上的戏剧演出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强有力的手段。
如此看来,打造一个精神共同体、反抗教会的正统性是近代欧洲王者在国家转型期的普遍诉求。尤其是法兰西在迈向君主制国家的政治进程中,自黎塞留开始的几代治国者皆有“继承希腊、罗马的遗产,主宰整个欧洲、亦即当时所认识的整个文明世界的野心”,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路易十三的两个首相黎塞留和马扎然准备了近40年,继位后的“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又追求了50余年(1661-1775)。
随后,当法国受英国革命影响转向民主政制时,启蒙知识人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等人同样看重戏剧的教育功能。因此,我们就值得关注这样的问题:“朕即国家”的王者与主张民主政制的启蒙思想家,都需要借助戏剧来实现某种政治意图,但他们作为立法者有相同的高明见识吗?
写下《王储训言》的第二年(1664),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举行扩建典礼,时年42岁的莫里哀受命为国王以及大贵族和教会高层演出新剧《伪君子》的前三幕。这出喜剧刻画了一个行骗的教士达尔杜弗,不料,此剧甫一上演就给莫里哀惹来政治麻烦,巴黎大主教佩列菲克斯对这部喜剧大为光火。这位大主教不仅是位历史学家,还是国王的告解神父和灵修导师,为了平息事端,路易十四不得不颁布了禁演《伪君子》的敕令。五年后(1669年),喜爱喜剧的国王才开禁允许上演,这一年,《伪君子》共上演37场,成为演出当季票房收入最高的剧目。
其实,在剧团被勒令禁演的五年间,勤奋的莫里哀完成了《伪君子》的余下两幕,还完成了另一部传世喜剧《恨世者》,1666年在法国宫廷首演时,这部新剧大获成功。剧中人阿尔赛斯特(Alceste)虽是个贵族,却被解读成对贵族德性的一种褒奖,这让莫里哀幸运地躲过一场政治麻烦。然而,由于涉及国家转型期出现的诸多尖锐的伦理问题,莫里哀的这两部剧随即引发争议。有人认为,从路易十四对这两场喜剧演出的反应来看,《伪君子》和《恨世者》即便不是采纳了国王本人的意见,至少也与国王的某种意图暗合。
莫里哀的《伪君子》模仿荷马的笔法,让笔下的埃耶米尔巧妙设计:说服奥尔贡藏身于卧房的桌子底下,好让他亲眼目睹达尔杜弗如何轻薄引诱女主人,如何肆无忌惮地嘲笑奥尔贡的愚蠢。最后躲在卧房的奥尔贡亲眼见识了达尔杜弗的丑态后,他这才如梦初醒,识穿达尔杜弗的伪善面目。要命的是,骗子达尔杜弗早已得到奥尔贡的家产授权,他以此要挟奥尔贡。就在这个家庭即将分崩离析的危急时刻,英明的国王犹如神之降临般出场,将达尔杜弗绳之于法,全戏落幕。
不难理解,《伪君子》向来被认为有政治意味:表面上以家庭纠纷为背景的市民喜剧似乎与政治无关,其实是意涵丰富的政治隐喻。但我们还应该说,这部剧作具有政治哲学的解释潜能。通过马基雅维利(1469-1527)的政治喜剧《曼陀罗》,我们就能理解,在欧洲近代王权国家兴起时期,喜剧创作实际上成了一种重要的政治行动。今天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的学者,绝不能忽视《曼陀罗》这部写于16世纪初的喜剧。因为,该剧的政治隐喻对于理解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所要表达的政治教诲必不可少。
《曼陀罗》甚至包含着马基雅维利“政治药方”最核心的部分,而《伪君子》与《曼陀罗》有着相似的情节模式和人物要素,恐怕并非巧合:两部剧作的基本情节都是男主人引狼入室,客人引诱主母。此外,两部剧作也都在展示:基督教士如何伪善甚至邪恶,男主人如何愚蠢,女主人如何无辜,机智的仆人如何充当串场线索。不过,《曼陀罗》意在展示如何巧妙地篡取他人家庭的治权,《伪君子》则要揭示教士的伪善,意在捍卫家庭的治权。
若将家庭比作国家,这两位喜剧诗人隐藏在喜剧修辞下的政治教诲则更为显白。《曼托罗》中的“情人”卡利马科精心策划,最终成功“夺妻”;《伪君子》中的“求欢者”达尔杜弗的最终失败则显得颇为勉强。如果考虑到意大利尚处于破碎的封建割据状态,而法国已经是统一的王权国家,二者与教宗国的关系有很大差异。若把法国比做一个被君主与教会争相夺取的“女人”——欲望对象,那么现实中的达尔杜弗已然成功。
换言之,莫里哀的《伪君子》在暗示法兰西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才能把这个象征国家的“女人”从教会手里夺回来,彻底根除政治共同体处于的双头统治的难堪局面。
当年,在凡尔赛宫观看《伪君子》的观众中,有不少教会的上层人士,他们看到如此不堪的教士形象,而国王却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当然会大为光火。路易十四下令禁演此戏以及五年后又开禁,恰恰反映出路易十四政治处境的前后变化:从顾忌教权势力到敢于置之不理。
人们甚至可以说,《伪君子》过早暴露了国王的政治意图。毕竟,其时路易十四亲政仅两年,为稳定自己的王位,他尚需要得到教会支持。用路易十四自己的说法,自己的责任和利益要求依靠教会以对付不同政见者,支持出世和世俗的教士,因为他们在困难时刻一直支持君主制。
为了稳固自己的王权,路易十四着手清除宗教改革带来的教派分离。为了统一法国的基督教,他一方面恢复高卢教会的旧仪式,同时敦促并且威胁信奉新教的大领主改宗天主教,下层社会的新教徒在赏钱的诱惑下也纷纷改宗天主教。一旦稳固王权后,路易十四就开始自主选任主教,不再理会罗马教宗的管辖权,法王与教宗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伪君子》恰好在这个时候上演,自然会引人猜测,创作《伪君子》的莫里哀可谓深谙国王的用心。
不过,《伪君子》中还出现了另一类型的伪君子,有研究者称之为“不自觉的伪善者”:作为这个家庭的暴戾僭主,奥尔贡就是这一类不自觉的伪善者,开口正直,闭口虔敬的奥尔贡,其实本剧最伪善的人,他的伪善也隐藏最深。
奥尔贡专断、蛮横、自私,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一家之主,日常举止刻意模仿贵族的做派。在家庭成员面前,奥尔贡极力维持自己的权威形象,显得既道貌岸然又仁慈宽厚。一方面,对于女仆的无礼和鲁直,他显示出一种罕见的容忍;可是对于女儿和儿子的反对声音,他却表现得极不耐烦,霸道而专横。此外,奥尔贡对伪教士达尔杜弗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连女仆道丽娜都看不下去,对他冷嘲热讽。可是奥尔贡却毫不顾忌,似乎世上唯有信仰值得他牵挂,除了信仰的化身——伪教士达尔杜弗之外的其他人,甚至他自己的家庭和亲人都显得无足轻重。
莫里哀没有明确展示奥尔贡隐藏在宗教狂热之下的内在动机,但是,我们很难把这种宗教狂热解读成单纯的愚蠢。若非奥尔贡的大资产者身份,人们大可怀疑,莫里哀的笔法在隐射国王路易十四。因为,奥尔贡的“宗教狂热病”虽然基于一种精明计算,却有着僭主式的专横。为了彻底拉拢宗教骗子达尔杜弗,奥尔贡不惜逼女儿玛丽雅娜与未婚夫悔婚,勒令她嫁给达尔杜弗,甚至将全部家财都转赠给这位尚未缔婚约的“女婿”达尔杜弗。为了惩罚儿子反抗,奥尔贡表现得十足象个暴君,他高声辱骂儿子,扬言要把儿子赶出家门。在第一幕第五场,奥尔贡对小舅子克莱昂特的一段告白或可视为他在为自己种种有悖人伦的反常行为辩护:听达尔杜弗讲话,我就变成了一个新人;他教我凡事冷淡,割断我对尘世的关联;我可以看着兄弟、儿女、母亲和太太死掉,就象这个一样,全不在乎。
作为妻弟的克莱昂特对奥尔贡“宗教狂热病”感到震惊,他惊呼:“奥尔贡,这可全是人的感情啊!”如果说专制君主的专横体现为弃绝属于人的情感,那么,正是教士达尔杜弗把奥尔贡变成了专制君主,奥尔贡却将伪教士视为自己变成“新人”的主要原因。倘若以上的推测不虚,那么喜剧诗人莫里哀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竟敢当面暗讽君王。
不过,莫里哀在《伪君子》一剧中主要批判的对象仍然上教士达尔杜弗的虚伪。莫里哀让我们看到,达尔杜弗对奥尔贡教诲的是“凡事冷淡,割断对尘世的关联”,反讽的是,达尔杜弗关于虔敬的教诲与他的行为相悖。因此,克莱昂特难以置信地质问奥尔贡:如此行事古怪,矫揉做作的假教士,却被他视为虔敬教徒的楷模。
无论如何,莫里哀借古罗马圣人卡图(公元前234–149)的名字暗示,在路易十四的时代,君主和教士都是伪善者,仅有新知识人有鉴别真假的眼光。如果说莫里哀对奥尔贡盲目崇拜达尔杜弗的刻画是向路易十四奉上最真诚的规劝,那么,这仅仅表明他对待教权和王权的态度有根本上的差异。
为求得路易十四解禁《伪君子》,莫里哀多次递交“恳请书”,在“第一次恳请书”中,莫里哀为自己作了如下的辩白:“鉴于伪善是诸种恶习中最普遍的一种,同时危害最大,也最危险。陛下,我的意见是,如果我写一部喜剧来贬责这些伪君子,把所有伪善的人惺惺做态的假面,和那些用虚假的狂热和猥琐的善行,费尽心思地诱欺世人的冒牌信徒,把他们暗藏的勾当通通曝光,这对于您王国中所有高贵的人来说,决非微不足道的善举。”
莫里哀知道,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喜剧诗人从不迎合普通人的趣味,喜剧借笑声来医治灵魂“疾病”,鞭打时代的恶习,这是莫里哀为喜剧申辩的理由。可是,为何莫里哀会认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恶习是伪善?为什么他认为,伪善在当今时代“最普遍”也“最危险”?谁是莫里哀在信中痛斥的伪君子?如果人们普遍认为,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指向教士,那么,路易十四后来解禁《伪君子》就证明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可是,难道路易十四没有从莫里哀对奥尔贡这个人物的批判上看出作者也是在规劝自己?倘若如此,那我们有理由推测《伪君子》一剧针对的正是路易十四执政初期与天主教会的合作。
与马基雅维利不同,《曼陀罗》以登徒子如何合法地巧夺他人财富和女人的喜剧,隐晦地教唆有政治抱负的人如何采用欺骗手段达成政治目的,《伪君子》的喜剧结局则表明:莫里哀力图展示的不是欺骗,而是他在“第一恳请书”中所说的“普遍的伪善”,即他视之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大的弊病——最普遍、最坏,同时也最危险。
伪教士达尔杜弗在奥尔贡的家里之所以几近成功实现其全部企图,正是基于两个受骗者——奥尔贡和他母亲的伪善。奥尔贡表面极其虔敬,实则自私、愚蠢且冷酷无情;他母亲白尔奈夫人以美德的审判官自居,然而,在这个大家庭里,上至奥尔贡太太下至仆人,无一不受到她尖酸刻薄的指责。她前一刻还在高调夸耀自已无可挑剔的慈善,下一刻就能反手给无辜的女仆一记耳光。作为新生的资产者,奥尔贡的人物特征就是虚伪、沽名钓誉。莫里哀在《伪君子》中力图展现的,正是这些处于国家转型期的新生资产者阶层的伪善面目。
前文提到,《伪君子》中仅有两个“明眼人”,哲人形象的克莱昂特和人民的“代言人”女仆道丽娜。似乎在莫里哀看来,克制伪善的良药要么凭靠理性的哲学,要么凭借自然质朴的天性。就剧情而言,“人民”的道丽娜显得比“哲人”克莱昂特更有行动力,她的言辞更为犀利、更为坦率。由此来看,将近一百年后,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同仁就戏剧问题论争时引用到莫里哀的作品,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毋宁说,莫里哀的喜剧中早已蕴含着后世启蒙哲人论争的萌芽。
阿里斯托芬的谐剧《鸟》,嘲讽高昂的政治激情,甚至嘲讽自然哲人对“天”的爱欲,看不到平常的、普通的事物;同样,莫里哀嘲讽的教士激情显然属于高昂的激情。因此《伪君子》的巧妙之处在于,莫里哀通过伪教士达尔杜弗之口讲出了真教士用以教育信徒的说辞,正是这种狂热的宗教激情让人看不到属人的情感和家庭生活的首要性。
或许,莫里哀的《伪君子》与路易十四的王权与教权的冲突无关,正如阿里斯托芬的《云》或《鸟》与雅典民主政制的兴衰无关,以及卢梭的《论剧院》与日内瓦的实际政治无关一样。毋宁说,他们的喜剧都与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人性激情相关,这是一种错误的、看似高昂的激情,包括智术师式的激情、教士式的激情或启蒙知识人式的激情。
何谓错误的、看似高昂的启蒙激情,值得看一看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的一段话:诗人有必要随时把最神圣的东西践踏在地下,要鼓吹凶暴的行为;对诗人来说,根本无所谓神圣的东西,道德也不例外;如果人物和时机要求这样做的话,他可以用讪笑来对待道德;当他对上天怒目而视,对神祗口出恶言,你不能说他褒渎神明;当他匍匐在祭坛前向神明做出椎心泣血的祷告的时候,你也不能说他敬神信道。
狄德罗的这番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卢梭为何反对启蒙思想家建剧院。因为卢梭心里很清楚,这类高昂的激情只会使“最神圣的法律,最珍贵的自然感情受到嘲弄”。由此我们更可以理解,卢梭何以在《论剧院》中以叙述体写了一出喜剧,甚至改编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并将其视为“在道德方面最好且最健康”。似乎在卢梭看来,即便莫里哀的喜剧有种种不足,也好过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戏剧。国家政体的转型肯定会搅乱普通人惯常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时代,一旦普通人赖以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遭到破坏,其后果当然不堪设想,历史的悲剧总是似曾相识。
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转型的时代,真正最令人担忧的“时代病”并非普通人的败坏,而是看似高昂的激情却让少数智识人的德性败坏。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戏剧批判,是莫里哀的喜剧相隔一个世纪后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