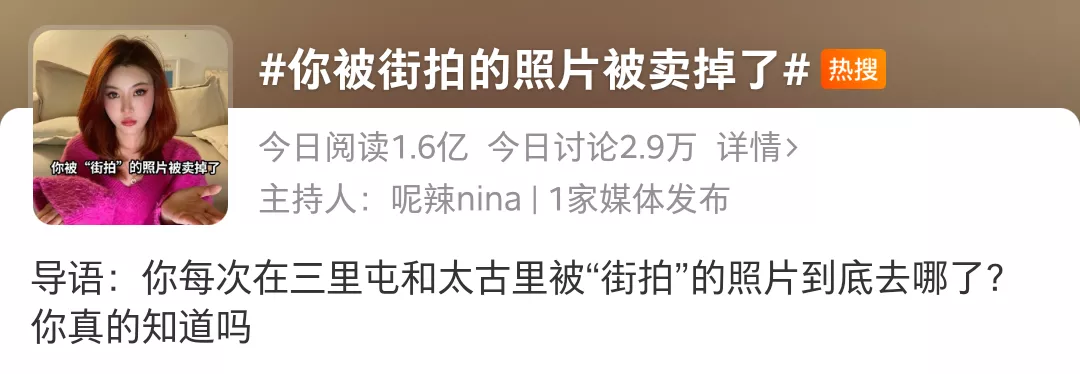局外人电影剧情「分析」
引 言
人能失去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唯有宗教不可或缺。宗教,人之根基。
加缪《局外人》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加缪以小说的形式对存在问题的加以探讨。时至今日,对于《局外人》存在之思内涵的探论仍是络绎不绝。人生的话题本就是绚烂多彩,重读《局外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存在的话题进行新的探索,对存在意义的新的追问。本文也是再此基础上产生,抓住存在的视角,通过对人的不可或缺宗教的论述,探索存在的意义。
时代背景下的追问与探索
(一)战火中的追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存在主义的中心由德国转向法国,因为法国在二战中曾被德国占领,法西斯统治让人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经历了痛苦和绝望,感受到生命的恐惧与孤独,以及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人们被悲观的情绪包围,烦恼和忧虑成为了人们的基本状态。人们特别希望能够找到一副精神的良药,人的自由何在 ,人应该怎样谋划自身,人的道德是什么,人要承担怎样的责任。人们开始思考这些话题,并对人的存在自身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在这些背景下,存在主义思潮在法国蔓延下来,并得到迅速传播。
(二)加缪的探索
加缪的短篇小说《局外人》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入狱前的经历,另一部分是狱中对自我的审视,逻辑上是以时间为主线的线性趋势。主人公默尔索经历了从人性升华为神性的精神历程。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蜕变,即使面临即将到来的死刑。默尔索的内心也能平静的面对,是什么让默尔索的内心发生巨大的改变?答案是克服了无常的命运,荒诞的世界和对死亡的恐惧。达到了圆触的宗教境界,圆触的宗教境界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人生三境界中的最高境界。那是一种消融矛盾的精神上的自洽性。
基于加缪的探索的两个论述
(一)论无常的命运
1.无常命运的本质
默尔索的命运是无常的,小说开始并没有为我们介绍默尔索的身份背景,而是开篇第一句就抛出了惊雷般的陈述。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小说以母死为矛盾线索,情节继续向下发展,母死,参加母亲葬礼,重新回归生活,偶然开枪杀人,被捕入狱,判处死刑。生活的一切原本显得井然有序,却因为思维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意外开枪误杀了一个混混,有序因偶发性事件瞬间转为无序事件。随即,无序状态又快速地恢复为有序的状态。对于一台电脑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短暂性卡顿,但却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系统性失序无可避免,又无法对其进行预测,无论是多么精确的计算,也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误差,这是数学方法的局限性,时间是线性的历史,永远无法解决芝诺悖论的二分法。在线性的时间上是无限可分的,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以至于更小的时间单位都是无限可分的点。这些无线可分的点却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那存在着发生任何事情的可能性。纵是极为不可能的事,只要基数足够大,就有概率发生,不可能即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一切事件都是概率性事件,因为随时可能发生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世界的本质属性即是无序的。
无序即人们所讲的“无常”,从字面上理解无常即没有常态,处于变化流动之中。倘若我们把人生看做为一个系统,无常即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发生任何事情的可能性,处于无序状态之中。这正是我们理性人所正在面对而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因为我们拥有的仅仅是过去和现在。至于,未来是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内容存在是不可知的。对于未知,人在心理层面是恐惧的,排斥的。人们在内心的深处潜藏着对未知明日没有任何把握的恐惧。这也正是人的宗教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我们需要方向。人们渴望着计划有目的去谋划着未来。希望一切都遵循着某种有迹可循的秩序运行,即有序的状态。有序即是已发生了的且符合人的期望预期,人把之称为有序,认为其存在为合理。事实上,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有序是非法的虚假性,有序是人在大脑中构造出来的美好意愿,人们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朝向自己的美好预期发展,都有计划性的发生,其实质是为摆脱对未知恐惧的需要。
2.关于人的内在需要
人,最初被抛入世界之中,对周遭的环境一无所知感到陌生,恐惧的情绪油然而起。为了缓解内心的恐惧,人要给自己找精神寄托,要给自己找个方向。所以说,人在恐惧的驱赶下,是有个朝向性的力,这也是人的宗教何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是可能性的基础。在黑格尔所论述的主奴意识关系里,自我意识的斗争中,胜利的一方的意识成为了主人,而失败的一方的意识成为了奴隶,主人是为了得到普遍承认而冒险献身的自我意识,而奴隶是苟活求生的依赖意识在于顺从主人的意志。可以说,奴隶是主动的,有需要的被统摄。哪怕这个主人会无情残忍的迫害他,只要制造恐惧仍是奴隶主维护统治的方式。因为在恐惧中,内心会迫切寻找依靠,获得心理的慰藉。所以制造恐惧,人的朝向性就会加强,整体就会更加紧密,更加听话。如上所述,人是会害怕脱离群体的。在群体中,恐惧感会得到缓解。哪怕是集体去毒气室,群体中的人也不会觉得有多么恐惧。集体中的恐惧感并不是会一直在处于被缩小状态。集体恐惧要么被扩大,要么被缩小。没有中间项。在心智方面,我们可以说,人最初团结在一起也是为了缓解这种恐惧的情绪。人不断的让自己忙碌起来,也是在转移注意力规避这种恐惧的情绪。外在条件(地理位置,环境,时代)和内在人的需求,共同作用下创造了我们的文明。我们一直以来的发展也是为了消解内心的恐惧感。未知增加了我们的恐惧,而消解恐惧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探索未知。文化、宗教 、自然科学等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的。甚至我们可以把这种恐惧感归纳为人的始动力。
这样说来,人从一开始就是奴隶,是这种恐惧的情绪的奴隶。这种恐惧的情绪才是主人。也就是,恐惧是自为的主人。毋宁说,人是和恐惧在争夺身体的控制权。恐惧逼迫着人,去消解恐惧。我们文明的根基也是基于此,为摆脱最初的恐惧,我们创造了神 。不同的自然现象有各自的神在掌握着。而神与神之间的故事,又联接成神话体系。人们为了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的需要,也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受客观条件限制,人们对客观世界中的自然现象所作出的种种神话解释,可以说是已经迈出了启蒙的第一步。再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神话已是启蒙”,而现在文明又朝向另一个人类所创造的新神话发展,即人类正在创造着一个以科学为名的神话,迷信科学和迷信鬼神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启蒙至此衰落为神话。综上。我们对人的宗教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度的内在刨析。
有序,只是人们美好的期盼,而无序或无常则是人生常态,命运或世界的本质。默尔索先生很幸运又很不幸的遭遇了无常的本质,幸运的是他触碰到世界的本质,发现了无上的真理,世界本就如此无常,存在即合理。而不幸的是在多数人眼中他的遭遇似乎是那么值得人同情叹息。而又到底是谁应该叹息呢?根据上述逻辑,我们已经论证了,世界无常的本质,有序的合法性也被推翻,虚假的有序并非常态。而仅仅是人类自身美好的意愿,渴望保持着某种平衡的状态,是生命内在本质的需求。
(二)论荒诞的世界
1.哲学视角下的荒诞世界
叔本华认为世界是人的意志的外延,世界之一切是人的意志的表象,倘若要更为精准的理解叔本华的深刻内涵,我们不得不提起康德的物自体,在康德看来,人的认识何以可能?是人认识事物的前提,是先天拥有一种认识能力,及其先验的认识形式,至于客观世界本身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而我们认识的世界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要有先验的认识能力,然后用这样的能力去认识世界。也就是说,人类认识的事物已经过了,人的先验认识形式的加工。而产生的表象认识,至于世界本身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可知,世界和我之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网,这个网即人的先验认识形式,人所认识的世界是从网中过滤的世界,是人的世界,是人的认识表象,从康德先验认识形式出发,世界是荒诞的,世界在此指“人的世界”我们认识的世界只是人通过自身先天就有的认识形式加工认识的世界,是人类的外在主观世界,是我们认识的所谓客观世界。例如,你面前的桌子,是通过你先天的认识形式加工后的表象,至于它是什么?我们无从可知,所以才有了“世界是我的表象”之类的话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对自以为所熟知世界本身是什么样子的认识,都是不可知的。这也恰恰印证了世界的荒诞性。
2.生活世界的荒诞
在加缪看来,世界的荒诞性表现在人与世界的割裂,从存在主义主场看,世界自身没有目的和意义,现实并不是合理的,这就让人产生了世界是荒谬的感觉。严格来说,世界人身并不荒谬,它只是存在那里,并不管人的理想价值,希望和意义,荒谬是源于人对世界的合理期望与世界本身这种方式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世界是此在意义上的世界,对于此在才有意义。简而言之,此在的世界被此在赋予了意义,世界上的一切都与此在,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此在将一切存在物赋予了意义,并用高度抽象化的概念去表述其所是。概念如同符号,符号是人与世界连接的中介环节。不同的抽象符号的组合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构建了此在世界的文明体系。毋宁说,我们的世界仅只是凭空而建的符号系统,而我们却对这套毫无根基的系统深信不疑。当具体的某个人某天忽然的意识到这个疑问,荒诞正向你袭来。当然,荒谬感的产生有各种途径,加缪对此有详尽的描写,比如在日常单挑的令人窒息的生活中,我们免不了会在忙碌中停下问一句:“为什么如此生活?”我们忽然感到日常生活毫无目的,我们的存在顿时失去了意义。
世界显得黯淡无光,具体来讲,当你开始不断地反问“为什么如此”的时候,荒谬正向你走来。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都要遵循着一种共同的习俗,上学的年龄就应该出现在学校,毕业了就要进行工作、结婚、生子,然后含辛茹苦的抚养下一代。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未来的轨迹已经被预设好了一样。人们逐渐走向了同一,人走向了大众,失去了自我的差异性,更为恐怖的是,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而那些用于挑战世俗规则,标新立异的冒险家只有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一是被世俗同化并加入大众之中,要么被大众以极端的方式予以唾弃或毁灭。德国哲学家尼采就是这悲剧中的冒险家之一。很显然尼采的思想超越同时代多数人的思想,不为大众所理解,为主流社会所排斥、打压,尼采的一生是孤独的,在孤独的绝望中,尼采疯了,仿佛是为这世间最为无情、残忍的反抗。尼采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到死后才出生”。
相对于孤独的尼采,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似乎更为悲惨。在母亲的葬礼上,默尔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没有和来参加默尔索母亲的来客一样发出阴阳怪气的哀嚎、哭泣,甚至没有在母亲封棺前看母亲最后一眼。在母亲的葬礼后,匆匆的返回公寓,大睡一场。他和女人游泳看电影滚床单,和大家眼中的不良青年成为了好朋友,默尔索所作的一切在世俗人眼中是那么碍眼,冷酷无情,以至于后来在法庭上,检察官用近乎嚎叫的语调控诉默尔索,怀揣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在法庭上,检察官对杀人细节避而不谈,反而列举了默尔索的几条罪状,妈妈死了,他连遗容都不想看。妈妈的棺材前,他喝咖啡还抽烟。第二天,又和新交的女朋友看电影滚床单。他的邻居兼好友是个混混。检察官以此为证据,让陪审团相信默尔索本性恶劣,杀人纯粹是蓄意为之。最后,陪审团被说服了,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将默尔索处以死刑。在陪审团看来,默尔索的杀人细节已经不是重点,他在母亲葬礼前后的种种表现,足以证明他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局外人》中仍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矛盾突显,用大众自以为合乎理性的逻辑和标准去判断对方的行为是否正确。事实上,对于大众而言,大众需要的并不是真相本身,而是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想法,达到某种目的。符合即是公正。法律的公正性也受到了质疑。虽以法律条列为依据,但仍然离不开人们的主观判断,人们用心理联想的方法和生活中的习俗习惯为标准,对可怜的默尔索先生进行审判。将事实与默尔索母亲逝世前后的表现联想起来,断定默尔索先生恶劣的本质。
荒诞的世界无时无刻的显现着其荒诞的本性。世界就是这样非理性的,充满神秘色彩的,说地震就地震,说海啸就海啸,说发洪水就发洪水,人是拿世界没有办法的。世界总是无视人的愿望,甚至是对人充满敌意的。在这种境况下,人是渺小而孤独的,甚至是绝望的。人和世界的疏离,正是荒诞感产生的原因。面对这样荒诞的世界,渺小而孤独的个体最终不得不走向人的宗教,挣脱精神上的枷锁获得灵魂的慰藉。
论存在之思
(一)默尔索的救赎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死亡的真实的临近激发出默尔索对生的依恋,默尔索的头脑中在无比的混乱却又在脑细胞无比的活跃中,一步步逼近自己那个叫真理的东西。“死,要死了么?”默尔索开始思索自己存在世上的意义 。他知道自己无需害怕,因为死亡是迟早的事,活着又是一件无所谓的事,那么此时此刻,被执行死刑的前期,他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他拥有的只不过是感觉而已。到最后,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都只不过是感觉而已。这种默尔索赖以生存的感觉到最后,却为他带来了死亡。那么,到底是默尔索不该存在于世还是这个世界本就是荒诞的?有问题的,究竟是谁?默尔索最后终于发现,即使他此生庸庸碌碌,每天过着重复的又不断被人误解的生活,他仍然不枉费此生,因为即使是在最无聊琐碎的每一个片刻,他对自己都是随时把握的,他忠于自己的感觉。纯粹的忠于自己。他已不怕这世间的任何东西,所有的仇恨和误解,所有的偏见和审判。他都不在乎。这正应了那句话:“道德判你死刑,哲学证你无罪”我想当人们仇恨的望向默尔索这个冷酷凶残的人时,也许他会回他们一个怜悯的眼神,怜悯他们在这荒诞的世界上,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活过,怜悯他们对真实一无所知。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默尔索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认清并把握了自己,抵达了自己的本质。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本身就是本质的显现,在最后一刻,默尔索实现了从人性到神性的跨越,达到了圆融的宗教境界。
(二)宗教概念的重新界定
现代人对“宗教”这一概念多保留着一定的警惕性,始终保持着同一种半怀疑半远观的状态,好奇而不靠近,广义上讲,宗教是信仰群体具体的某一派别,而从哲学意义上讲,宗教,应是人的根基,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宗教。宗教一种精神性的象征,属于社会意识,个人意识层面,并不可或缺。那么,宗教具体是什么呢?宗教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或人生信条,尽管这些信仰或许可能相似,可能相差甚远。简而言之,一句话,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宗教。宗教又有个人宗教和集体宗教的区别,集体宗教指人类群体或全体,都有某个共同目标为方向,比如我们的国家就以”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目标。努力奋斗,人的文化、道德、法律等等一切人的生活中的元素,都在朝向着某一目标发展,这一目标,我称之为“体系化”。体系化如同建立一栋类似于三角形的理论大厦。地基也就是基础,框定了其范围,也就是规定性。然后朝着某个方向去向上构建,最后发展为目前的最高成就,并不断地向前发展。人的文化、制度、道德、精神、法律、秩序等都有这个特点,都朝着某一方向,都在朝向着哪。就连我们的社会历史也逃不过这样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存在,而存在本身就好似柏格森教授的绵延一样,处于一种连续的流动状态的河流一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包含着对方,又彼此各有差异。正如黑格尔所言,哲学就是哲学史。同理,我们亦可说文学就是文学史,世界本身就是世界史,是其存在史。存在本身就是正在流动的,正在流动就代表存在处于发展之中。存在本身逐渐的发展史就是所谓的历史,过去就是现在,现在包含着过去的种种。过去从未过去,一直隐隐的存在于现在。
(三)人的宗教
人生在世,我们都不开自己的宗教。人,总是需要一个方向的,总是要为自己的灵魂寻找归宿的,这是人内在的驱动力—生命意志,所决定的。人自身总是有个朝向性,总是指向某一个方向,并以此为目标准则,指导或指引着自己前行。可能,我们中多数人意识不到我们所拥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我们事实上的宗教,指导我们世间的人生信条或者信仰,通过我们做出某一判断、某一原则,并肯定其价值的真理性。这套流程的实质是在个人宗教的指导下完成的。你所相信的、你所理解的正式你独一无二的宗教,我们从宗教中获取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鼓舞着自己前行,纵是世界是荒诞的、命运是无常的、死亡在无时无刻的逼近。痛苦与苦难并行,但宗教却予以我们的力量,焕发出生命意志的光辉。克尔凯郭尔认为大多数人停留在人生三境界中的前两个境界。一是满足肉欲、二是对自己进行道德上的把握,只有少部分人菜能达到宗教境界,认识并把握自己,纯粹的忠于自己。很显然,默尔索在最后的时光里达到了这个境界,人们常常认为宗教总是与所谓的迷信虚无的神保持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其实不然,纵是,真的有神存在也仅仅是人的神。因为,只有人的神,对人才有用。神的神,对我们又有何用呢?“神”只是有限的人对无限的向往一种表达方式。神,不应该被神化,人自身亦是神,能用非常人思维去理解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对于常人来讲,就是“神”。“何谓神?”神即道,道法自然,真如。
有限的人总是朝向一个至高的无限。例如,道德领域的至善、形而上学领域的逻各斯、宗教领域的神。显然,默尔索先生在人生最后的旅途中,接近了最为本质的东西,实现了从人性到神性跨越,达到了内心永恒的安宁。世俗中的人是杀不死一个圆满的神的,只能遥不可及的仰望着。人本身就是极为矛盾的动物。无论你希望得到什么,想要成为什么,喜欢活着爱上什么,对什么产生欲望,形成执念。你就为什么所束缚。而束缚你的正是你坚信的信念,也就是你的宗教。人的渴望和追求固然是一个作茧自缚的过程,然而只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经历过不尽其数、难以言喻的日夜,经历过独自绵长漫无目的的挣脱,几经穷途末路,你才会迎来破茧成蝶那一天,宛如仙神。如同黑塞的小说《悉达多》中悉达多向好友乔达文谈论佛陀时说:“老师的生平经历,比他的教义更加重要,因为那才是智慧真正的来源,而每一个真正生活并体验过的人,单单是他的存在,对其他人而言就是最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