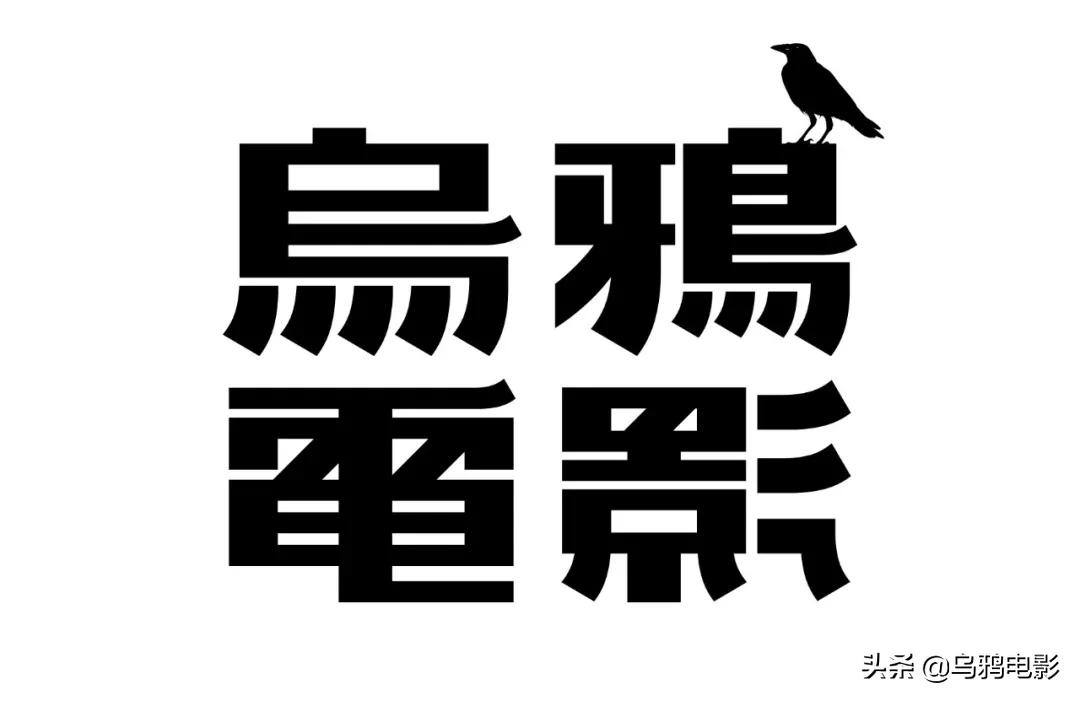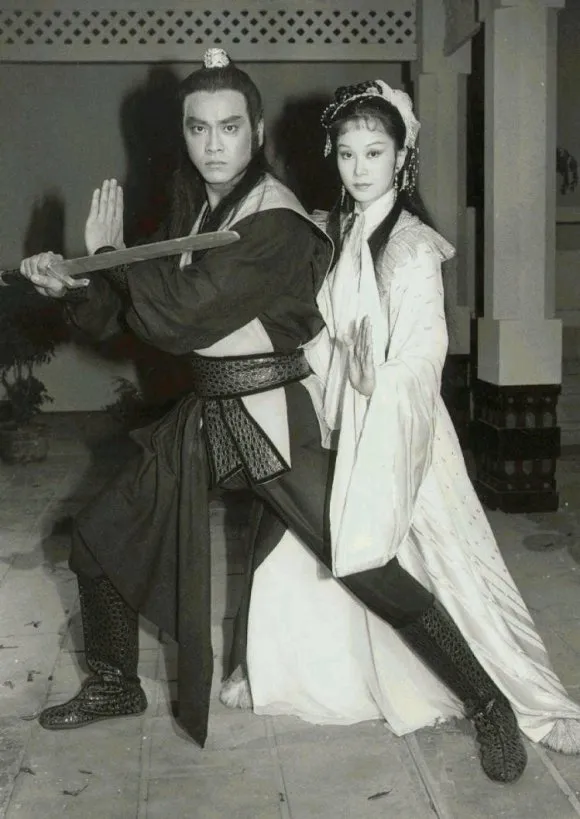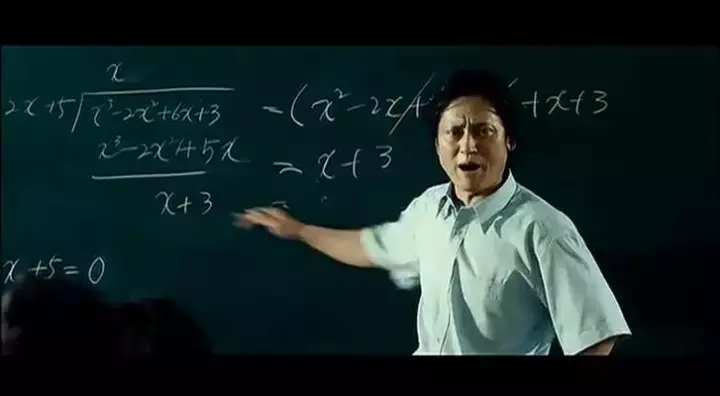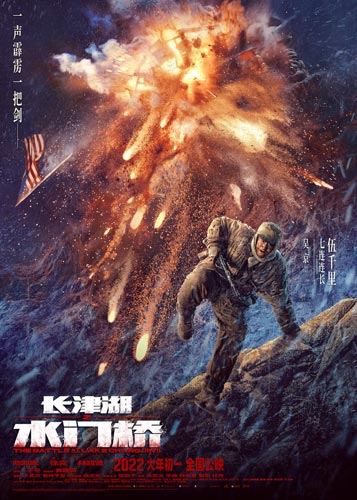莎拉钥匙电影剧情「分析」
先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冬赛馆事件”。
冬赛馆全称是“冬季自行车竞赛馆”,位于巴黎。1940年6月,抵抗了两个礼拜后,法国宣布向德国投降,并在维希建立傀儡政府。这个政府为了维护法国领土的完整,不惜与法西斯展开各项合作。比如派遣军队打击盟军、协助纳粹捕杀犹太人等。
1942年纳粹要求维希政府交出16-50岁之间的法国籍犹太人,为了表现自己,法国政府将所有16岁以下的犹太人抓捕,包括刚出生的婴儿。7月16、17日,巴黎一共抓铺13000名犹太人,其中包括4115名儿童,他们先是被集中关押在冬赛馆,然后父母和孩童被强行分开,前者被分批送往奥斯维辛,后者被关押在巴黎郊区的集中营慢慢死去。这批犹太人最终只有两千名活着回来,这两千人中没有一个是孩子。
这场屠杀有一个很诗意的代号,叫做“春风行动”。
据统计,二战期间一共有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和这个数字比起来,13000和4115这两个数字实在“不值一提”。
所以,这件事甚至都没有被写入法国的历史课本。但是,总有人不愿意轻易抹掉这段历史。
《莎拉的钥匙》就是围绕着这件事而展开的。
莎拉是一名犹太小女孩,1942年7月16日夜,警察抓捕她们一家的时候,她只有十二岁。为了保护年仅四岁的弟弟,她把他藏在家里一个秘密壁橱里,并锁上了小门——她相信自己很快会回来,重新恢复正常生活。
被囚禁在冬赛馆数天之后,她们一家被送往集中营。在那里父母被送往奥斯维辛,而莎拉却得到别人的帮助逃出生天。但当她回到巴黎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弟弟死在了壁橱深处。六十年后,记者茱莉娅有机会调查此事,她发现自己的夫家——泰泽克家族竟然和这件事有关——莎拉她们家被抓走后,泰泽克家族住进了这套公寓,但他们丝毫不知道壁橱里面有一个孩子。当莎拉回到物是人非的公寓,看到自己死去的弟弟和被霸占的房子,她对法国彻底绝望,于是远走美国,最终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选择自杀。而泰泽克家族知道了这件事后,竟然向后代选择了隐瞒。
看完这本小说,我心里的疑问远远多于感慨,而且我知道这些问题或许永远也没有答案,或者可以这样说:回答这些问题是件残忍的事情。
比如这个问题:到底存不存在“人性”这个东西?
我们一直忙于争论“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或许“人性”本身就是一种虚构。
有人可能觉得我这么想有点残忍,但我想说,相信“人性”的虚构,正是对人类继续持有希望的前提。
如果不这样,我们怎么理解奥斯维辛?怎么理解春风行动?怎么理解南京大屠杀?这些历史无一不证明人性之恶。
如果有人性,那么人性是残忍的。
犹太人在长相上与其他欧洲人非常相似,警察要想准确辨认出他们孰非易事,这个时候,“热心的”巴黎市民“踊跃地”举报了自己的犹太邻居,即使这些邻居上个礼拜还曾帮他们看护自己的孩子。
莎拉一行人被押往冬赛馆的时候,她们坐的是巴黎的公交车。在此之前,她每天乘坐同一班车上学,负责开车的仍然是那个很熟悉的公交车司机。押解她们的法国警察中,竟然有一个曾经护送过她过马路!而眼下,他们却失去了往日的和善,转脸就变成了冷酷的凶手。肮脏的人性一夜之间毫无保留地袒露在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面前,她感到自己“一瞬间成为了一个老女人”。
如果有人性,那么人性是冷漠的。
1942年7月16日夜晚,冷清的街道突然吵嚷起来。巴黎的市民不会听不见这些异常的响动,但很少有房间的灯亮起来。大家几乎都在黑暗中推开窗户,默默地旁观着一群于己无关的人被押往死亡之路。即使有零星的抗议,也很快被警察呵退。
这13000人在被押往郊区的集中营时,曾经倒过好几次火车。这意味着在那个夏天,不时会有一大群衣衫褴褛的人踉踉跄跄地突然出现在巴黎的火车站,甚至要穿过位于铁轨之间的市镇。那些被呻吟声搅醒好梦的人们,他们初时惊惧,后来也就嘟囔着翻个身——他们知道这些无辜的人是去赴死的,可是然后呢?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谁让他们是倒霉的犹太人呢?
如果有人性,那么它绝不是一个完整的、可理解的整体。
除了纳粹分子和傀儡政府,还有很多普通人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屠杀。首先当然是那些执行抓捕命令的警察;还有那些巴士司机——是他们开着自己那班公交车运送犹太人去冬赛馆的;还有火车司机——是他们运送犹太人前往集中营的;还有铁路工人——那些铁路是直接修往集中营的,他们不会不知道自己所修的铁路是用来承载亡魂的。
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在此之后也是。他们可能从来不会想着去杀一个人,甚至不愿意去妨碍另一个人。但他们却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一场大屠杀。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参与,这场大屠杀才会那么高效。我在想,他们是怎样成功地说服自己从事这场勾当的呢?
“我不过是在奉命行事?”“这不过是我的职业?”如果没有勇气抗命不遵,那他应该有勇气放弃这份工作。
“就算我放弃,肯定会有别人这么做——每个岗位都不缺新雇工,这么一来,我的不合作就没有意义了”。确实是这样,无论你放弃与否,这份工作肯定能做成。但是你可以因为放弃而免受良心折磨之苦,这个代价还是合算的。
我不知道自己的猜测算不算准确,而且作为一个置身事外的人去批评他们,本身就是一件算不得高尚的事情。
我还想知道,这些“帮凶”们,在战争结束后,他们过的怎么样?他们还能不能顺利地重新做回一个善良的平凡人?如果可以,那么我的猜想就是正确的:人性不是一个单纯的整体。
现在恐怕有人愿意相信“人性”是不存在的了,因为相比于这个,“人性存在但天生为恶”更让人绝望。
人性本恶不仅会让我们顿失改造自己的勇气,甚至可能让我们永远得以回避自己的罪恶,或者,毫无负担地坦承自己的罪恶——一切都是人性的错,我作为被动的执行者,只能对所犯的错误深表遗憾。除此之外,我爱莫能助。
把历史上的弥天大错简单地推诿给一个空虚的概念,这或许是继奥斯威辛之后,我们的又一个弥天大错。